|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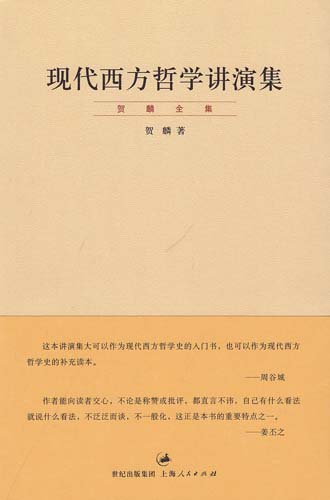 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没有哪一代人能像“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如此复杂的命运和际遇。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有幸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又赶上大规模出国留洋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在思想文化上具备了融合古今、会通中外的条件和能力,一大批学术巨匠由是而生。 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没有哪一代人能像“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如此复杂的命运和际遇。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有幸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又赶上大规模出国留洋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在思想文化上具备了融合古今、会通中外的条件和能力,一大批学术巨匠由是而生。
今年9月20日是中西兼通的一代宗师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9月23日是贺先生去世20周年。经过五年的编审和集结,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出版的《贺麟全集》权威定本目前已推出七种,包括贺麟先生四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文化与人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近代唯心论简释》;另有黑格尔《小逻辑》、《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和斯宾诺莎《伦理学·知性改进论》三本经典译作。
贺译《小逻辑》被认为是“严复《天演论》中译本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译本”。《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黑格尔:黑格尔学述》、《马克思博士论文: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也将在今明两年陆续出版。
拜梁启超梁漱溟吴宓为师
1902年9月,贺麟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一户乡绅家庭。他8岁入私塾,后来入新式小学和中学。 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1920年春,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贺麟闻讯即前往听讲。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精研入微,他融精深学识与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求知若渴的贺麟。贺麟从此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拜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梁启超和梁漱溟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1924年,吴宓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聘有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吴宓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与另两位好友张荫麟、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
多年的求学生涯使贺麟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1926年8月,贺麟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28年2月,贺麟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大学毕业,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但因不满在芝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又在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贺麟再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怀特海等著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从1931年回国起,贺麟长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在组织和领导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名重一时的哲学家。
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
贺麟的“新心学”创立于20世纪四十年代,这是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贺麟看来,经过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但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展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的输入表面上看似乎是坏事,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西洋文化学术上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它“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贺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介绍,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还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
相较于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而言,贺麟的“新心学”在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中是比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新心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在新儒学的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或许正因其晚出,因而能对此前的新儒学思潮作出公正而恰当的评判和总结,因而能合理地吸收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理论缺陷,从而使“新心学”的面貌与其他新儒学颇为不同,更具圆融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