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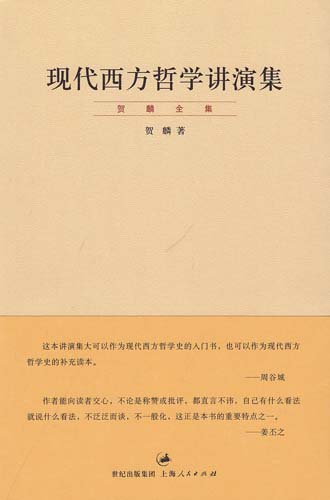 贺麟先生的弟子、本套丛书主编张祥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贺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不了解贺麟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无法真正知晓现代中国如何引入、消化西方哲学,也会盲然于新儒家运动一个重大思想源头。而要深入研究贺麟,此《全集》就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文本。 贺麟先生的弟子、本套丛书主编张祥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贺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不了解贺麟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无法真正知晓现代中国如何引入、消化西方哲学,也会盲然于新儒家运动一个重大思想源头。而要深入研究贺麟,此《全集》就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文本。
贯通中西哲学
贺麟,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又先后到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麟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麟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
1942年,贺麟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张祥龙认为,作为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介绍,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还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生两大成就
张祥龙在评价恩师时,认为贺麟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打通两者。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直觉法。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摩相荡而一气相通。
另一个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他志在向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是在选题择人、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译本。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者的领会。
张祥龙认为,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处,能真正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他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