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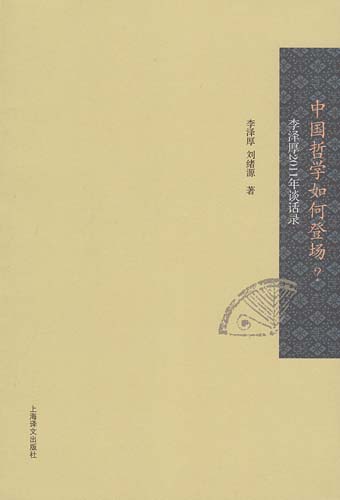 四个“静悄悄” 四个“静悄悄”
刘:我们上一本对话出版后,读者对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很感兴趣,你在那里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有些本来不喜欢理论的年轻朋友也爱看,他们大多读过《美的历程》,是把对话当你的传记看的。这次你也谈一点自己的故事吧。你的生平应该就是“珍惜、眷恋、感伤、了悟”的经历,从你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忧惧,到现在的“为人类”而活,也可说是“寻求意义”的一生。
李:我没有那么多故事,一生简单平凡,“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上次说了。我还说过,我有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静悄悄地读——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我的任何书印数不少于一万册,读者都是一般的青年、干部、教员、企业家、媒体人、军人,等等。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还不止一两个人说读我的书找到了人生意义、生活价值,这大概是学者教授们读不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我有证据,例如各种报纸经常有他们谈读书的文章,说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乱七八糟的书都有,就从没发现有谁在读我的书(大笑)。我的书既没宣传,也没炒作,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这非常之好。我非常得意。小时候父亲和我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印象深刻,至今记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
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刘:还有两个“静悄悄”呢?
李:去年说过了:静悄悄地活———近十年,我的“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基本上执行了。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像是演讲,实际还是杂七杂八地回答问题。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今年大都婉谢了。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昨天,我们的责编陈飞雪打电话来,问起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以谈谈。我对自然科学一直感兴趣。上次我也说过,中学里我理科成绩好。初中时的平面几何,一些习题很难,但我喜欢做。训练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比如画虚线。八十年代我写过文章,说初中要学好“没用”的平面几何,高中要开逻辑课,这很重要。据说现在把逻辑放在政治课里,这有点搞笑。因为逻辑如同语法一样,恰恰是没有阶级性的,这还是斯大林说的,毛泽东也说逻辑没阶级性,它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我真不懂为什么放在政治课里讲,与政治毫无关系嘛。
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
算是毕生遗憾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
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二十七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
在莫高窟我待了一个月,每个洞都看了好几遍。那时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可以随时去看,不像现在。和敦煌研究所的人来往很少,就是自己看。(打开当年的记录)你看,这里都记了,每看一个洞,都做记录,主要记自己的感受。至今还记得,当时很想做敦煌壁画藻井图案不同时代装饰风格的研究,如唐的自由舒展而含混,宋的清明规范而呆板,联系唐喜牡丹宋重松槐,以及唐宋诗的不同,觉得是非常好的美学题目,可以从审美趣味的变迁看人类心灵的积累和丰富。我一直有几个很想做的实证性题目,却始终未能做。算是毕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