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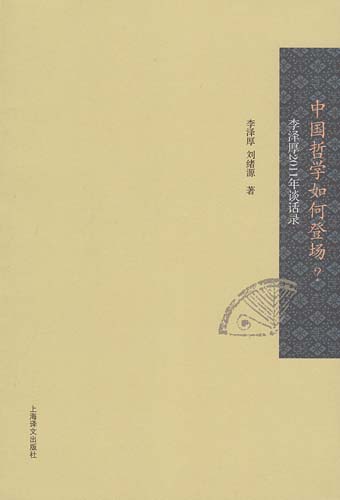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先说,说说为什么要出这个续集;我再作补充。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先说,说说为什么要出这个续集;我再作补充。
刘绪源(以下简称刘):好。《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年4月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有十几家报刊做了转载转摘,还登上了好几个图书排行榜(有的连续几周或几月,甚至排到了榜首)。我们不追求这个,但一本谈哲学的理论性的书能有这样的销售业绩,终究还是令人高兴的事。译文出版社趁刘再复回国的机会,就这本书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有不少人提出,这个题目还可以再谈,还没有谈够。
李:远不够。这可能是无穷的,至少是一个广阔话题。
刘:还有就是关于书名——“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很多人认为它很醒目,暗含一种提醒:哲学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有可总结的东西,可以上升为哲学理论,而这又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李:大家可能没注意这书名后面的问号,其含义有二:一是这命题能否成立?二是如果成立,如何可能?
刘:这两点,正是大家所议论的。所以也有人认为,书名太大了,和它比起来,书的内容又显得单薄了。
李:非常单薄!但就是再续谈三次,也还是单薄。这是留给大家和后人的一个题目,我是做不了了,《哲学纲要》序里说了谢幕,八十多岁了嘛。我希望大家来做,使中国哲学有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性登场。
研讨会的记录我看了,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说谈得不够具体。但要非常具体,也不可能,哲学只是一种意见,不同于科学,科学要大量非常具体的经验材料。但“积淀说”、“情本体”、“度的本体性”等等,不大可能。第二个意见,是缺少论证。关于哲学的论证,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也常常不论证。
刘:不过回头再看,比如关于“情本体”,谈得的确是过于简略了。你的哲学思考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学是第一哲学”和“以美育代宗教”,包括“天地国亲师”信仰的“天地”如何理解——也就是你提出的“与宇宙协同共在”这一“理性的神秘”,还包括“巫史传统”,包括如何用中国传统消化和填补海德格尔,等等,这都和“情本体”有重要联系,有的就是它的直接组成部分,都还没能好好展开。如果这些方面能谈得详尽些,“情本体”的理论就显得更丰满,对你的观点的来龙去脉能看得更清楚,你的一些新的思考也可以容纳进来。我想读者一定会有兴趣的。
李:那好,我们就试着再谈谈。一、不要和上次重复,完全不重复也许很难,尽量少一点。二、在可读性上,在总体质量上,不要低于上次。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做到?
刘:能吧。李:很勉强。如果不行,就缓出或不出。我有点担心,因为你这次提出的,几乎都是理论问题。你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我都带来了,包括你发到美国的那份,在那上面我还打了不少标记。当然我把过去书里说过的东西更通俗地梳理一下也许好读点,但毕竟还是枯燥,而且更无条理。
刘:这些问题我精心挑选过,我觉得它们对读者来说仍有很强的新鲜感,是大家所关心的。至于条理,我们用对话方式单刀直入,直指人心,也许更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对专业读者也有专著之外的另一种参考价值。即使有些话题已在书中谈过,再谈还是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上次谈话从初稿到定稿,短短几个月时间,也能看到发展的踪迹。所以这次谈话不仅会通俗生动,我相信也一定会充满新意。
李:我不太相信你说的“发展”。这本印数应该少一点,不要印了卖不掉。
刘:我想不会。对有一定理论兴趣的人来说,好的理论,比听一般化的、重复雷同或编造痕迹明显的故事,不知要好到哪里去。我就宁可看有趣的理论书,也不愿看那些悬念横生的电视连续剧。我想本书的读者,至少一半以上,都是我这种人吧?
李:那好,试试。我们尽量让它好读一些,不要光说理论,说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我也尽量讲得浅显、生动些。有人会斥为“根本不懂哲学”,或“算不得学术”,且不管他。
刘:好!
李:还要说明一点,这两次对谈涉及的一些材料,多凭记忆,信口开河,未能逐一查核,很可能有错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上次将萨特与海德格尔并提、王国维谈诗人与哲学的选择之苦,虽大意不差却不十分准确。此外,谈话随意,时有跳跃,遣词造句,不及推敲,凡此种种,希望读者鉴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