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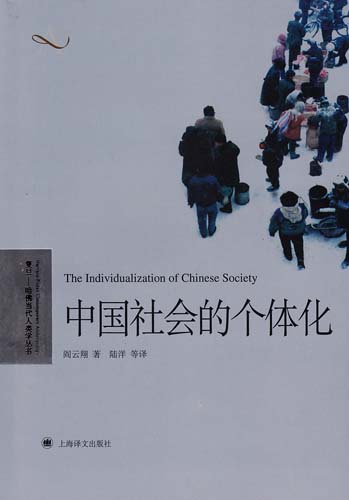 我认识的两三位法学专业的高校老师,现在给新生做勉励报告时,都习惯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做总结陈词。狄更斯不可能想到过,《双城记》头上这几句正确的废话被饱览世态的中国老师奉为金律,用来婉转地表达他们对社会状况既阴暗又切实的认知。 我认识的两三位法学专业的高校老师,现在给新生做勉励报告时,都习惯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做总结陈词。狄更斯不可能想到过,《双城记》头上这几句正确的废话被饱览世态的中国老师奉为金律,用来婉转地表达他们对社会状况既阴暗又切实的认知。
在《“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一书的序言里,阎云翔的判断——中国人有成为“无公德个人”的风险——看了让人怵然:这几个字足以引起对一系列恐怖的新闻事件的联想:助人被讹的、撞人捅8 刀的、女童丧生路人不救的,等等,这些事件的特点在于,一旦周知于众,听者很自然便会把自己代入为故事可能的主角,从而一面产生并日益加深对生存维艰的认知,另一面进一步降低对自身的公德要求。阎云翔暗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伴随着普通人的无公德化,伴随着对“公民”二字题中之义的减损。
追溯公德败坏的根由,必然首先想到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个体逐渐“脱嵌”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框架的时候。摆脱过去的桎梏之后,个体并未能进入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自我”中国》将之主要归因于国家对社会自治的遏制;而事实上,那种自上而下的遏制存在了太长时间,以至于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去创制、运行一个建立在一系列默认共识之上的公共空间,从而沦为“道德流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权利意识苏醒之后,人们不觉得承担与之相应的义务是应该的,反而产生了一种观念上的优越感,认为设法只取不予、取多予少是生存的基本智慧,或者,对另一些人而言,是对过去损失的理所当然的报偿。
阎云翔2009年的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汇总了他的一些田野考察论文,相当一部分内容取材于他的故乡——黑龙江下岬村的变迁。论尖锐度,这本书尚不如《“自我”中国》,作者对个体化前景持观望态度更多些,不过仍有一些小片段,折射出“最坏的时代”的迹象。阎云翔写道,新一代农村青年在结婚索要彩礼方面比上一代人要“贪婪”得多,他们声称自己“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只是通过彩礼要回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钱”。这个理论的逻辑漏洞很容易被揭穿,因为很显然,父母抚养子女长大和供给子女吃穿的代价必然远超过子女有经济收入后对家庭的回馈,然而对这一事实,那些借着结婚勒索父母的年轻人便视而不见了,甚至公开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人善人欺、马善人骑”)为“道德”。“个人主义的幌子”是阎云翔给出的中肯的界定。
人文学者或许理当以学术写作来保存道德,来标举值得追求的善。但是,阎云翔的论述一直保持着某种“学术零度”的调子,轻易不碰评是论非的尺子,这当是作者的自我约束所致。这些论文是阎在90年代至新世纪初陆续写成的,那段时间,人文学者多少都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召唤,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直面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会看不到商业化社会远非过去能比的道德腐败,但同时,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自己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就这个进程而言,再怎样思虑周全的学人,也必然要硬着头皮地心向往之。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这一困境被冲淡到了几乎无色的程度,我想,这与作者选择农村来考察有关。此书第八章“如何做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似乎可以看作对社会性道德危机给出的一个反例,甚至是解答:并不是非损人不能利己,本案例的主角王先生是一个能妥善利用道义经济环境的人,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把自己的家庭打点到富裕的程度,其秘诀是时刻保持“成本- 回报”的计算,且“所有的算计都在人情伦理的架构中完成”。不过,阎云翔指出了他在下岬村只是“少数被公认为凭借个人能力和勤劳而致富的人之一”,我们或可以就此理解为大多数富人都在攫取财富上落下不义的话柄。而且,我们一定会想到,农村的熟人社会是这一案例不可忽略的背景,而集体性的公德沦丧总是在一个更大的“风险社会”里发生,由迭出的个案拼嵌出一幅惶恐的图景。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谈到人心惟危时,条件反射地援引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记忆,最凶悍的一些声音,都将罪责推给了那些背离第一代领袖所划定的道路的人。他们都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60余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扎实地进入过公共道德生活,而是从一个个随时装填教条的道德空杯嬗变为冷拒一切教条的道德虚无分子;在一些可能上演“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场合,中国人往往表现出畏惧、怠惰和漠然。慈继伟在《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一书中做了如下的论断:
在这一道德滑坡之前的不是道德的繁荣,而是政治的胜利;后来的道德瘫痪无非是政治方案的失败而已——社会只能靠暴力、靠便利、靠懦弱、靠习惯以及靠一点点残存的简单人性来维持。
慈继伟道出了中国式个体化的崛起建于其上的根基。一个完全讲求实用主义的社会秩序,已失去了鼓励社会团结的有力的道德理由。很有可能,听着“时代辩证法”步入成年的我们,最后也都将成为这个时代挣扎成长的垫脚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