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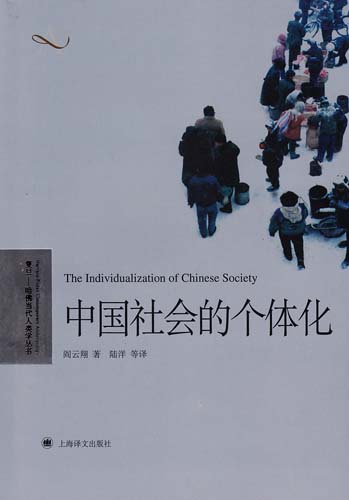 2005年,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以下简称《私》)中译本自序的结尾处,阎云翔提问道:建国以来的家庭改造运动,费尽移山心力地从宗族罗网中解放出来的,为何不是运动初衷所期待的独立自主的新人,反而是自私自利者?作者坦承《私》是部未竟之作,他给自己,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两年后,对第二次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的阅读让阎云翔醍醐灌顶,使他觉得找到了走出迷宫的门径,这次领悟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以下简称《中》)一书的选编和出版(《中》,第4、386页)。《中》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阎云翔于1992-2006年间发表的十篇论文,它们均是阎云翔顿悟之前的作品,倘若仅以此为论,《中》实属多余。赋旧文以新光彩的,是《中》的导论、结论和附录。在这三个部分里,阎云翔利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对各篇论文进行了深度解读,从整体上梳理了建国后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使《中》成为一部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精彩对话。阎云翔试图在《中》里回答《私》的遗留问题,它自然成为了《私》的续篇和新发展。 2005年,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以下简称《私》)中译本自序的结尾处,阎云翔提问道:建国以来的家庭改造运动,费尽移山心力地从宗族罗网中解放出来的,为何不是运动初衷所期待的独立自主的新人,反而是自私自利者?作者坦承《私》是部未竟之作,他给自己,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两年后,对第二次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的阅读让阎云翔醍醐灌顶,使他觉得找到了走出迷宫的门径,这次领悟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以下简称《中》)一书的选编和出版(《中》,第4、386页)。《中》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阎云翔于1992-2006年间发表的十篇论文,它们均是阎云翔顿悟之前的作品,倘若仅以此为论,《中》实属多余。赋旧文以新光彩的,是《中》的导论、结论和附录。在这三个部分里,阎云翔利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对各篇论文进行了深度解读,从整体上梳理了建国后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使《中》成为一部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精彩对话。阎云翔试图在《中》里回答《私》的遗留问题,它自然成为了《私》的续篇和新发展。
贝克以其风险社会理论饮誉学界。完整的风险社会理论包含了风险社会和个体化两个命题,这一理论源自对当代西方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型的观察。贝克强调,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几乎在其未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属于何种家庭、位于哪个社会分层位置、将会从事的职业、未来的家庭伴侣,以及拥有的价值观也是固定和确定的,不容置疑。与传统社会没有给人过多的选择机会不同的是,现代福利社会把人从家庭、阶级等传统的社会束缚网络中解脱出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都以个体本位原则进行设置,个体行动能力加大,个体不再需要他人就能存活。当代社会中的个人处于一种被逼选择的状态,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高速变迁,每个人都必须快速地做出一个接一个的人生选择,婚姻、职业、投资,各种成功学和生活指南风行于世。个人的每次选择都可能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但无论是价值标准还是家族网络都不足以构成个人可以依靠的避风港湾。现代社会中,社会只保障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出生即“被抛”,个体有着表面上的选择自由,同时也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风险社会理论因此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味道。
地处黑龙江省南部的下岬村是阎云翔的第二故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起,他在那个村庄生活和研究过多年。在长期的观察中,阎云翔发现该村的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自1980年代开始,父母包办与主导的婚姻淡出视野,自由结合的比例越来越高(《私》,55、71页)。以往交流少、情感淡漠的夫妻生活,逐渐被澎湃的激情所取代,人们更加强调配偶间亲密无间的重要性。三代人、两对夫妻同住一屋的传统居住格局被打破,首先是夫妻和未成年子女在家里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房间,然后是婚后迅速分家别居的浪潮涌起(《私》,131-135页,162页)。伴随而来的是家庭中权力格局的变化,父母在家庭中地位下降,儿子儿媳敢于挑战上一辈的权威,村落中的舆论也倾向于支持年轻人的观念,老年人景况堪忧。阎云翔在《私》的结论中不胜感慨,“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259页),“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261页)。
阎云翔发现,吊诡的是,造成当前农村无公德个人出现的源头却是解放后对个人进行的集体化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进行了集体化改造运动,个人从原来的家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本意是打破传统,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类,而这恰恰完成了个体化进程中的第一步:脱嵌(《中》,355-357页)。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中的工分记录制度,使年轻人发现了自身对于家庭的重要价值(《私》,178页;《中》,191页)。毛泽东时代,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被看作资产阶级毒草,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抨击,人们认为个人主义等价于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私利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对个人主义并非全面的理解一直流传到今天。在集体化努力失败后,人们奉西方生活方式为圭臬,这种曲解的个人主义凤凰涅槃般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中》,22页)。贝克个体化命题中的个体化与第一次现代化中的个体化的关键差别在于,第二次现代化的个体化是制度性的,它不是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没有主动性,同时也就不具备经典个人主义所包含的自强、独立、平等等内容。阎云翔认为,无公德个人的形成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