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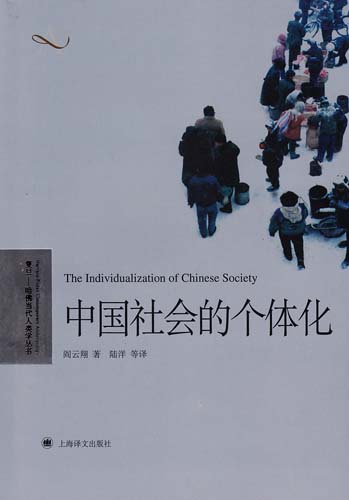 如今,说一个人有个性,通常是一种赞誉,而在不久之前,国人还不太习惯这样称赞别人,更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称赞。个人不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有时甚至还通过相当夸张的方式来表现自我,人们也毫不迟疑地相信个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其命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宣告完成。 如今,说一个人有个性,通常是一种赞誉,而在不久之前,国人还不太习惯这样称赞别人,更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称赞。个人不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有时甚至还通过相当夸张的方式来表现自我,人们也毫不迟疑地相信个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其命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宣告完成。
确实,虽然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主要选取的只是黑龙江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其中发生的变化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个体不再愿意为集体和家庭的延续而牺牲自己、在公共生活的真空中追求个体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年轻消费一代、年轻女性对家庭等级制度和代际权力关系的挑战……凡此等等,都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让人感到历历在目,因为这一切事实上也是三十年来我在老家农村所经历和看到的情形。
个体权利的苏醒,最初源于权威的崩溃和撤出。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1978年之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社区收缩的过程,对村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切实而重大的改变,虽然它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
我出生于1977年,恰好经历了这一过程:幼年时母亲还要每天出工去挣工分,后来虽然抓阄分地;20世纪80年代中的乡村干部也仍能依靠其政治资本享有一定的个人威望,至少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了进村办企业而请他们吃饭。然而逐渐地,一切都渐渐开始崩塌:社场慢慢倾圮成一堆废墟,最后平整为土地;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也不会再去给乡村干部送礼,有纠纷时也不再理睬他们的调解;年轻人既不愿务农,更不在意任何权威,他们想的只是离开这个困住他们的村庄,去追寻自我实现。将年青一代与其父辈相比较是最能醒目地突出这一变化的:他们不仅讨厌农活,不像父辈那样还对乡村干部有一定的敬意,甚至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乡村干部。
这一幅图景,如今回想起来错综复杂、交替进行,但其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我”自己的发展和权利。
作为一个从小在乡村社会长大并目睹这一切变迁的人,我对阎氏所描述的场景并不陌生,但有时“熟悉”也可能成为一个劣势。阎氏虽然在下岬村生活了十多年,但作为一个插队落户知青及后来的社会学家,他的身份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外人”,这使他一直能清醒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社会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要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去熟悉化”,这样才能发现意义。但同时,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像是把这个乡村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而甚少去体察乡村社会某些特定概念对人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处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偶然,两者相互促进。法国学者Louis Dumont曾谈到法国自由主义认为“个体解放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始与终”;如今的中国确实已是他所说的个体主义社会,即“最高价值体现在个体中”。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由的个体往往都是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是国家需要严厉防范的人物,相比起来,如今确实是“换了人间”。耐人寻味的是,现在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与古代游民类似的特点,如“主动进击精神”(王学泰语),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从一个熟人社会过渡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如何让个体在获得解放后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减少其破坏性,则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