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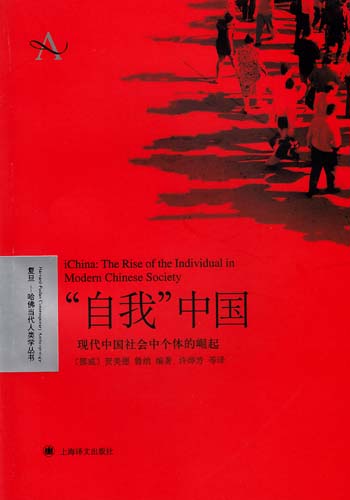 “在中国,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发展不仅决定了私人领域,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也决定了经济的组织方式和灵活的就业,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人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各章节也从不同的角度表明这一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它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单纯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 “在中国,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发展不仅决定了私人领域,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也决定了经济的组织方式和灵活的就业,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人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各章节也从不同的角度表明这一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它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单纯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
这段摘自乌尔里希·贝克夫妇为《自我中国》所撰写之前言的文字,几乎全然道出了我对该书的阅读兴趣所在。对应于文中相对宏观和抽象的描述,我所想到的更多是如今sns网站与微博上那些频频可见的,彰显着新生个体/自我的种种言论;是那些铺天盖地的以表达自我为出发点的图像与文字。确乎然个体化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进而,我开始追问:在这些我十分熟悉的日常现象中,在书里的田野调查中,有哪些要素是足以定义或标志中国式个体化呢?
当“个体化”被冠以“中国式”这一定语,在逻辑上便很有必要先去了解西欧或是美国的个体化究竟为何?然而这样的探寻将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入乌尔里希·贝克或是鲍曼的理论构架。为了避免理论阐述所带来的晦涩,在此我暂将欧美个体化进程简单概括为:个人逐渐从各种血缘的,社群的,文化的,阶层的种种制约或是群体中脱嵌(detach/disembed)而出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打工潮”对应了中国最明显和直接的脱嵌现象,那么欧美的个体化进程则直接追溯到了工业化的初期。不难发现,单就现象层面而言,两者之间不无共通之处。
只是,国内“打工潮”的出现与其说是与改革初期中小企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倒不如说是与政府推动下的市场经济化和消费主义化密切相关。或者用贝克夫妇的话来说:“中国的个体化路径是在以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受时间限制的顺序发展。中国在个体化尚未得到宪法的支持之前就已经对经济以及日常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实行了新自由主义式的解除管制。”在这里,贝克夫妇的言外之意是:与欧美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式的个体化如同行进在经济和消费的单行道上。
表面上看,贝克夫妇的这一对比多少有几分“欧洲中心论”的嫌疑。然而,一旦当我们将上述的嫌疑与论争通通悬置,将目光投向那些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具体的个人/个体时,我们便能实实在在地从当下生活的细节中感知到”中国式”这一定语的内涵。
尽管只是为《自我中国》一书中的若干独立研究写作导论,阎云翔所给出的(对“中国式”的)阐释却在不经意间喧宾夺主,成为该书中最有洞见和最能呼应贝克与鲍曼理论构架的论述,而紧随其后的第一,二章的田野研究却更像是对严著的修正和补充。
在导论中,阎云翔引用了自己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的结论,指出:“由于国家对社会自组织和自治社会的敌意,日渐崛起的个体已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具有成为我称之为 ‘无公德个人’的风险。日渐崛起的个体大多受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而自我主义则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间的交往之中”。
阎对于“公德”的重提,在我看来恰恰是冒着被“日渐崛起的个体”当成冥顽不灵之说教者,道德卫士之风险的。只是,为避免语汇所引发的纠缠,我自己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切入来理解和回应严所提到的“公德”。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之所以新崛起的个体会仅仅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义务与他人,实则是因为在这些个体的心目中并没有,或是缺乏对于“社会”这一概念的深入体认。“社会”成为了一个其含义不证自明的词汇,被理所当然地使用。然而使用者却并不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社会”究竟所指为何,也就更加无法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有利于“社会”, 才可能成为某种“公德”。
有趣的是,在暗中呼应我上述解读的,正是本书的中英文书名之间的对照。从书封上我们可以看到,中文的“自我”所对应的英文是“I”;也即“自我中国”= “iChina”。与此此时,若对中文的“自我”进行拆解,我们会得到“自”+“我”。不论是基于我自身的观察还是书中的田野,对于大多数崛起中的个体/自我而言,自=自由;从而他们对于“自我”的理解也就等同于“自由的我”。
不难发现,在这样一种对于“自我”的认知中,“自”被等价为“自由”而凸显,而“我”却是如同“社会”那般被理所当然地忽略掉了。也正因为此,英文书名中的”I”才显得弥足珍贵。”I”而不是”me”,这暗示着一个主格/主动的“我”,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我”。 然而,主体性却不是可以不劳而获,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在对社会的参与和认知中逐渐成形。并且,在这一主体性的构建过程中,他人所扮演的是一面面小镜子,而由他人所组成的社会则扮演着一个更加巨大而抽象的他者,一面巨幅却并不清晰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