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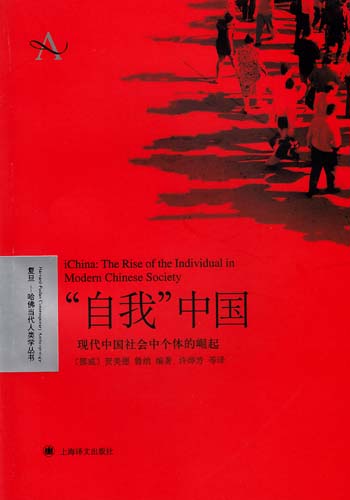 随着国际人类学研究逐渐从边缘文化走向中心区域,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学者书写民族志的舞台。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最新译本——《“自我”中国》来源于十多位中外学者的跨界努力,内容则基于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经验调查。“个体化”,这个具有明显西方现代性色彩的概念,如何在中国的框架下得到延伸,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正如贝克夫妇在前言中强调的,中国的个体化“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欧洲的个体化是第一次现代性胜利的结果,普遍在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展开,中国的个体化,却注定要在没有制度保护的土壤上展开,充满着张力和变数。 随着国际人类学研究逐渐从边缘文化走向中心区域,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学者书写民族志的舞台。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最新译本——《“自我”中国》来源于十多位中外学者的跨界努力,内容则基于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经验调查。“个体化”,这个具有明显西方现代性色彩的概念,如何在中国的框架下得到延伸,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正如贝克夫妇在前言中强调的,中国的个体化“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欧洲的个体化是第一次现代性胜利的结果,普遍在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展开,中国的个体化,却注定要在没有制度保护的土壤上展开,充满着张力和变数。
贺美德与庞翠明在对中国农村青年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后发现,如今的农村青年确实更强调自己的主观性并向往一种冒险的生活。然而,由于基层自组织的薄弱与精英循环受阻的现实,这种对于个人选择的理想化导致的是一种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他们不关心政党政治与村民选举,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主要源于是否能为“自己及其家人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在对农村养老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许多身体健康的农村老人都更加倾向于单过,他们正在主动适应现代化带来的农村结构的变化,选择了一架自由与风险同时加码的天平。但是,农村社会服务的匮乏和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化却是这种生活方式变革的阻力,当老人们终有一天生活无法自理,之前回避的赡养问题还是必须要面对。德尔曼与殷晓清将视野聚焦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考察以孙大午为代表的农村企业家如何在公共讨论中既质疑官方的主导叙事,又避免在国家层面挑战制度的根基。作者引述狄克森的研究成果称,民营企业家“更关注的是在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中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第四章中,对于海滨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实证调查一方面发现了志愿者们顺应个体选择与动机多元化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中党和国家的干预。青协必须定期举行意识形态浓烈的学习讨论会,志愿者自身发起的活动亦很少得到共青团和政府的支持。而“没有得到任何党组织分支担保的有组织的活动,普通老百姓有时是会回避参加的”。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考察中,魏安娜发现了作家们反思和构建个体的努力,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作品中流露出的“他者性原则”,“即个体认可承担不同角色或身份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努力尚未创造出完全独立自决的主人公形象。而鲁纳在考察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后更是指出,尽管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文化运动中,个人的绝对自由和自治受到倡导,“对于个人自治与社会道德的政治关注仍把个人锁定在建设国家的角色中”。余凯思将中国法律与个体的关系分成了几个阶段,从封建社会的群体成员属性决定罪行轻重,到民国刑法的更看重“罪犯的个性或者犯罪行为背后的个人因素”,再到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与再教育,最后演变为当代充满争议的司法改革。但是总的来说,当遇到法律问题时,“二十世纪以来几乎中国各个时期的政府都更多地视个体为义务承担者而非权利享有者”。最后,李明欢对于华侨农场变迁的叙述描绘出了一幅逆个体化的图景:当改革进程拉大了个体间的差距,那些在财富的积累中被边缘化的群体,本能地形成“一种对既往集体主义时代的怀旧情结”,从而要求回归国家的庇护,收回失落的特权。这种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留在农场的归侨侨眷们开始构建一种“爱国华侨”的新型群体认同,以作为与国家谈判的资本。抗议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巨资推行“侨居造福工程”,逆个体化的诉求最终得到了国家的回应。
有趣的是,尽管该书的副标题为“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但是全书给人的总体感觉,却是中国个体化的不成熟与不彻底。与其说个体的独立性正处在普遍崛起的过程中,不如说他们只是在改革的罅隙里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而已,有人希望取消更多的限制,也不乏有人美化集体“逃避自由”,在从控制到自由的渐变光谱上,个人所站立的位置往往并非出于权利意识和内心信念,而是以功利目的为驱动。那些正在萌芽的个体意识,也在官方严密的把关下,左支右绌,动辄得咎。除了过分乐观的书名,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取了《“自我”中国》这样宽视野的题目,却对整个个体化图谱的建构着力不够。八章共八个主题似乎都只是点到为止,相互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如同一块只完成了几片的拼图,既猜测不到全景,也观察不到细部。除了第三章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访谈外,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案,某些调查的代表性似乎也不够。倒是阎云翔老师在第一章前所作的导论《自相矛盾的个体形象,纷争不已的个体化进程》,完整地梳理了“个体化”的内涵,以及个体化在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去年,阎老师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此篇导论与该书的前言和结论有相近之处,也是对其个体化思想的总结,切不可跳过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