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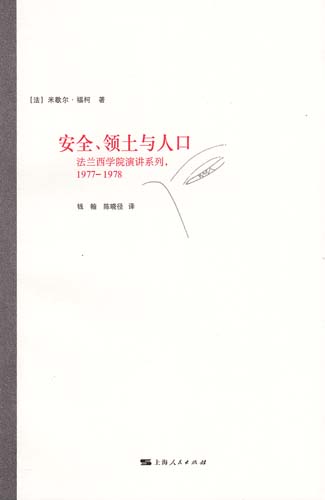 《安全、领土与人口》是福柯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题目。“安全机制”是福柯经常论述的主题,因为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是福柯主要的关注对象。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奇怪:领土和人口属于什么问题?在一般的权力分析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一般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夺的内容。难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了吗?虽然福柯并不忽视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但他总是把这种战争纳入到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思考,在1976年的授课《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就试图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命题翻转过来,从战争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1]不过,《安全、领土与人口》这本书并不是相同的思路,它所谈论的依然是国内政治权力问题,也就是对对人的治理和人口的诞生[2]。要想理解这本书,关键是厘清两个概念的谱系学:治理和人口。 《安全、领土与人口》是福柯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题目。“安全机制”是福柯经常论述的主题,因为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是福柯主要的关注对象。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奇怪:领土和人口属于什么问题?在一般的权力分析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一般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夺的内容。难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了吗?虽然福柯并不忽视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但他总是把这种战争纳入到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思考,在1976年的授课《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就试图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命题翻转过来,从战争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1]不过,《安全、领土与人口》这本书并不是相同的思路,它所谈论的依然是国内政治权力问题,也就是对对人的治理和人口的诞生[2]。要想理解这本书,关键是厘清两个概念的谱系学:治理和人口。
Gouvernement,在本书中大部分地方译为“治理”。这个词在一般情况下译为“政府”,是政治权力的运转制度和机构,但是在本书却几乎没有办法把这个词译为“政府”或者“政府治理”,而只能译为“治理”。因为福柯在本书中试图重建的是“对人的治理”的整体谱系,现代的政府管理体系只是这个治理的最新的一个形态而已。他认为,从基督教会对人的治理到现代政府的治理是一个连续体,从希伯来的东方传统到近现代的政府组织方式之间有某种根本的一致性。对人的治理不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而是希伯来的牧领制度进入欧洲之后逐渐在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牧羊人(即教会及其高级神职人员)和他们所牧养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前者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后者,而且要引导他们走向灵魂的拯救。这种负责是全方位的,所针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在基督教的牧领中,牧羊人既对羊群负责,同时也把每只羊看得和整个羊群一样重要。在马太福音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3]福柯反复强调了基督教治理的这一特点:牧羊人对每一只羊都要负起具体的引导责任。然而15和16世纪,西方的牧领制度遭遇了重大危机,教会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席卷欧洲的基督教改革并没有取消引导,只是更换了新的方式。基督教时期的国家的治理术以家庭治理为范式,与中国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相似,把修身、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续体。
在欧洲的传统理性中,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获得最终的拯救;而国家的问题与此相应,传统的国家理性所设想的是重建对应于天国的人间的罗马帝国,欧洲的君主国都笼罩在罗马帝国逐渐远去的光辉所投射的影子之下。然而,罗马终于渐渐隐去,各个王国的君权也就不再关心时间的尽头和最终的拯救,而是确保当下和将来的现实生存。群体的行为和生活开始成为国君的治理目标,新的国家理性逐渐形成。传统的治理艺术主要针对精神领域(智慧、公平、美德等等),此后则转向一种特殊的知识和对象,君主权力所针对的目标是对人群的治理,这就构成了新理性的孵化器。而新的治理术不再把家庭作为国家的范式,范围和数量的扩大导致质的变化,“人口”与一群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以家庭为模式来考虑国家治理问题:治国和齐家变成两码事。
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治理艺术的问题就与新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相互联系起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成为君主们优先考虑的目标,在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两大主题:一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导的原则,尽可能确保欧洲各国力量的平衡;另一个则是所谓公共管理(police)[4],“即一系列必要的手段,用以在国家内部增长国家的力量。在这两大技术的结合部,作为共用的手段,就是国家间的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致富,人们期待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出口的增长,并获得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时代,人口-财富的组合是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5]”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各个国家权力运行过程的优先问题,对人的治理从具体的个人转向了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人(être humain)才有可能变成“人口”(pop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