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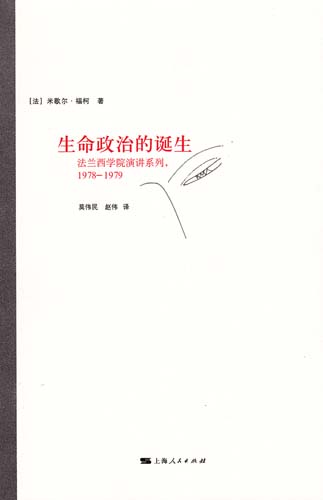 一 一
大凡看到题目新颖的著作,读者们想必感觉如获至宝:期待读到一部富有创造性的学术作品。我初见本书亦然,但读后却陷入了沉默—不是源于期望落空的情绪,而是因某种东西欲寻不见。后来某日读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所引用的一句话,方释然长叹:原来如此。在一次讲座的开始,为分析近代西欧国家行事的理由,福柯引用了一位叫贝伦森的艺术史家于暮年时说出的一席话:“上帝才知道我是否害怕原子弹把世界摧毁,但至少有一件事我同样担忧,那就是国家对整个人类的侵犯。”福柯概括说,这是“一种国家恐惧症的最纯粹、最清晰的表达”,并且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主题。”国家,准确地说是对国家的认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欲寻不见”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这种对国家的恐惧症状历久弥新,但20世纪的独特经验—包括1920年代出现的苏维埃、德国纳粹主义、战后英国的计划运动—使得这种症状的易感人群对“国家”,对以国家为工具的专制、暴力、独裁敏感异常。既然患病,那么除非自暴自弃,人们自然会去寻医问药。结果,法律与秩序的关系得到了反复的探索,“法治国家”最终成为对症的处方。对于粗通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人们而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过,福柯却更进一步。通过对“疾病”、“犯人”、“疯人”等一系列近代西欧国家出现的范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国家没有本质。……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福柯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国家的理解,并非这里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读者面临的问题可能完全相反:对国家的无意识。
问题正出现在这里。当福柯说这种“国家恐惧症”是“我们”所熟悉的主题时,有多少中国学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属于“我们”的一员?又有几人堪称“熟悉”这个“主题”?这么说绝非苛责中国学者未染上“恐惧”重症,而只是想低声询问:中国学者缘何近乎先天性地丧失了对国家的免疫力?—这里的“中国学者”自然是指部分而言,而非一个不漏。当他们面临各种问题而诉诸国家时,他们如何未曾想到:问题可能正是国家所造成的,国家正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观念中并非没有国家;但那是一种与“国家恐惧症”全然不同的东西,用“国家幻想症”命名之,庶几可得其神髓。通过幻想,“国家”被抽象为正确、正义的代理,一种实现幸福的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幻想肩负国家建设的重任,与国家融为一体,学者们自己也光荣、伟大起来。
这种“国家幻想症”的表现形式林林总总。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表现为学者对“国家框架”—诸如“国家视角”、“国家建设”、“国家任务”—无反思、无批判、甚至是无意识的设定。这种状况反映了学者对“国家”性格与品格的不理解。“国家”究竟为何物?熟悉近代政治思想的人们会说,那就是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不错;但问题在于,这个说法是如此粗糙,以至于它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掩饰了问题自身。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的诞生通常被刻画为一部英雄史诗;国家被视为统帅子民们进行反抗、进行建设、追求繁荣的某种行动的、人格的化身。于是,以这个“(民族)国家”为前提的研究,充斥了最近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诸如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借助这个未被质疑的、因而是可疑的“国家”框架,我们的生活诚然得到了某种刻画,得到了某种有序化;然而,我们因此而付出的认识上的代价,却不可胜数。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情形可以说是“神义论”在世俗化社会中的经典表达。如同上帝一样,国家被视为永恒正确的行为者;即便显而易见的过失或差池,也被解释为国家“正义”的某种体现—这个有着神性的国家会发怒,会让人恐惧,让人费解,但其根本目的却是将正义带给人间。它让人敬畏,因而让人幻想,让人感到安慰。
这样一来,这个结论就水到渠成了:“国家恐惧症”与“国家幻想症”原来竟是亚努斯的两副面孔;人们因恐惧而幻想,因幻想而恐惧。不过,这两种症状的临床表现和最终结局却截然相反。前者激发人们揭示国家的本来面目,因为恐惧来源于无知;克服了恐惧,就有了过上真正幸福生活的可能。而后者却将希望寄托于国家的善意自身,通过希望、憧憬、信仰来克服恐惧,换取虚假的幸福。人类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前者将人们引入理智的世界,让人们至少过上尘世体面的生活;而后者却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