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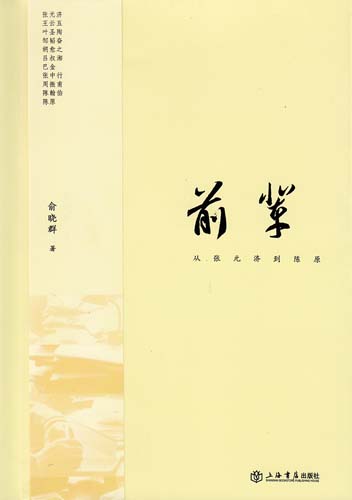 新近推出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出版人俞晓群对现代十一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作为“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作者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娓娓道出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等前辈出版人的故事,以及对于书业历史和现状的思考。 新近推出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出版人俞晓群对现代十一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作为“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作者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娓娓道出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等前辈出版人的故事,以及对于书业历史和现状的思考。
陈翰伯:让人难忘的红色出版家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翰伯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参加《读书》杂志的服务日。作为《读书》创建者之一,只要有时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会来的。会议照例遵循着“没主持人,没主题,没开始,没结束”的《读书》风格,与会者照例轻松自如地交流;但这一次,陈先生却没有“照例”操着他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侃侃而谈。他说过几句话后,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目光宁静。身边的冯亦代问他怎么了?他说,只是觉得很乏力。冯先生劝他要珍摄,他神情低沉地望了冯先生一眼,没说话……
翌日凌晨三点,陈先生起身小解,与夫人说几句话又睡去了。早晨,他的双脚犹有余温,心脏却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时年七十四岁。
陈先生就这样静静地去了,恍然间已是二十年的光景。前些天我读到沈昌文先生的文章《从陈翰伯、陈原讲起……》,文中说这二位被戏称为“CC”的老首长,是他毕生崇敬的导师。这话是沈先生的口头禅,我亲耳听他说过许多次。在沈先生的引见下,我有幸与陈原相识,亲手出版了他的多部著作。说到陈翰伯,我就有些茫然了,难道是他的早逝阻断了我们精神的交流?或者说沈先生等人的敬重之情,仅仅是因为他漫长而辉煌的革命生涯,因为他做过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等高位么?不会吧。
我开始找寻陈翰伯先生的资料。我发现,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人生的经历极其丰富,但留下的文字却少得可怜。一本薄薄的《陈翰伯出版文集》,一本《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二○○○年,在宋木文呼吁下,商务印书馆以上面两本书为基础,再次整理出版一册《陈翰伯文集》。仅此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按照陈先生自己的划分,所谓“青春办报,皓首编书”,他在三十五岁前以新闻为职业。他一九三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十一月即出任西安《西京民报》总编辑,那时他二十二岁。一九四五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七年任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他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名声很大;他曾把这些文稿剪贴成十几大本,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交给上海一位熟人保存。上海解放前夕,那人怕祸及自身,竟然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这也是他留下文字极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陈先生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暨《学习》杂志编委。一九五八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直至“文革”初期。就这样调来调去,留下的文字自然不多。到了“文革”时期,还会有文章么?说来奇怪,前几天沈昌文说,有人从潘家园淘到一些商务印书馆的旧档案资料,其中有一大摞陈翰伯的文字,有自传,有检讨书等;那人找到沈先生,还送给他一些复印件。
“文革”结束后,陈翰伯的文字依然不多,大多是一些讲话稿和回忆录。其中《老生常谈话文风》一文,最让我看重。它其实是陈先生对《读书》的一段批语,沈昌文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个批条,将其收入《想起陈翰伯同志》一文中。它大约写于一九八○年,是给《读书》提的十一条意见。其中写道: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总理、英明的领袖;不要用“千里传友情”之类看不出内容的标题;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话头;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不要用谐音式的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名称或某某编写组署名;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伯英雄排座次”等等。
读陈先生的“十一条”,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噢,想起来了,前些年,我们请沈昌文先生审读《万象》杂志稿件,他不是经常用这样的形式与口气教导我们么?他还告诉我们,陈先生曾经严肃地对他说,永远不要向读者说“应当”如何如何,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这就是文化传承啊!我终于在沈先生那里,找到了与陈翰伯先生精神沟通的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