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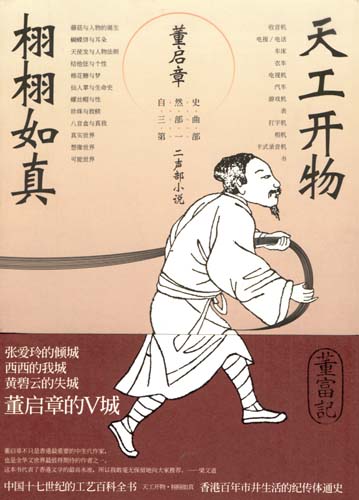 “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 “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
有孤独感,但没有忧郁
星期日:梁文道用把牢底坐穿来形容你的写作精神,在香港写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董启章:从他的角度看,可能觉得是这样的一回事,我自己却从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我本身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在外面活动,所以长期处于封闭的写作状态,并不觉得受困。这只是个较为沉静的状态而已,物质上没有束缚,精神上更是十分自由。
星期日:你认为,香港有没有纯文学?在香港从事纯文学,是否会面临养不活自己的窘境?
董启章:香港文学就是纯文学,这是我个人的定义。尽管有人认为香港文学驳杂不纯,我还是认为,香港最好的文学作品,始终是纯的。我们看刘以鬯、西西、黄碧云、韩丽珠等不同辈代的作家,都是在追求日常、通俗以外的文学性的。至于从事文学养不活自己,这在香港是常态,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没有作家会因此而感到困窘。我们应该庆幸在香港文学创作不能成为一个职业,因为这样写作就可以是一件完全自由的事,就可以回到它的根本。
星期日:写作的绝对孤独,让你感觉形同在太空漫游。骆以军为此得了忧郁症,他身边还有不少朋友自杀了,你有这方面的心理困扰吗?
董启章:虽然是有这样的孤独感,但我没有忧郁。我相信香港作家在这种事情上比较有免疫力,因为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从来没有幻象,也因此不存在幻灭。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文学是多么孤独的一回事,所以就比较不会出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而当孤独变成创作的必要条件,那就更加没有抑郁和抱怨的理由了。
星期日:为什么你拒绝写专栏,那样不是可以赚更多稿费来支持你的写作吗?
董启章:我对专栏没有偏见,但我不是一个适合写专栏的人。除了写小说,我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感,也没有每天写出来的必要。规定自己每天或定期要写几百字,说一些本来没有必要说的话,对我的写作和生活是一种干扰。至于稿费,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
作家不应该有粉丝
星期日:北岛说,粉丝对作家写作是一种伤害,他不要有粉丝。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董启章:北岛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读者和粉丝是不同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找到读者,这是环绕着作品发生的事情。粉丝往往忽略作品,而把注意力投放在作家身上,如果作家接受这样的事情,而且乐在其中,对他的创作会慢慢产生很坏的影响。换句话说,他将会失去独立性,因为他开始顾虑到粉丝的存在,和重视粉丝们对自己的喜爱。作家不应该有粉丝,因为作家应该随时准备好通过作品去冒犯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读者。粉丝却是不能冒犯的,粉丝只容许你去讨好他们。
星期日:内地市场会是港台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吗?
董启章:我没有这个想法。什么是“好起来”?没有内地市场就“不好”或者“好不起来”?我不知道台湾作者怎样看,以我所知,香港文学作家从来没有什么“不好”,卖书不多读者不多从来不是问题,也因此无须靠内地市场去让自己的状况“好起来”,更谈不上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地说,“市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写作中是完全没有位置的。
星期日:你的创作状态相当纯粹,不考虑市场、不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有时候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一种力量,让你可以做到如此决绝?
董启章:这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力量,几乎从一开始写作就是这样,只考虑自己能写出怎么样的作品,而不考虑这样的作品会得到怎样的接受。没有任何挣扎或需要克服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一个传统素质。我只是从前辈身上继承了这样的素质,过程毫不费力。
不艰苦不潦倒,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星期日:你说过,你不能想像有人把你任何一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因为改编本身很恐怖,最好不要做。可是大部分作家都十分期待此事,这也是你的一种骄傲姿态?
董启章:我相信当前对文学最重要的事情,关乎到文学作为文学存活下去的事情,就是让文学做只有文学能做的事。就写小说来说,就是让小说做只有小说能做的事。任何其它形式更胜任的事,应该由其它形式去做,而不是由小说去做,然后再以其它形式再做一次。我不反对别人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样做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但我对这样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也绝对不会在写作的当下作这样的考虑,因为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形式。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骄傲,而是谦卑,因为我只在写作的范畴内做一个作家能做的事,而不觉得自己可以在任何范畴占尽利益和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