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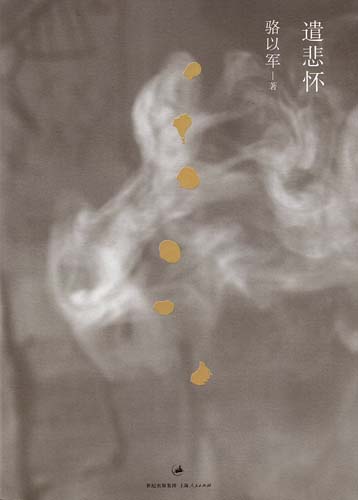 上海书展上,骆以军和董启章形影不离。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同年出生,是很好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在认识对方之前,最初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作品。 上海书展上,骆以军和董启章形影不离。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同年出生,是很好的朋友。对他们来说,在认识对方之前,最初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作品。
骆以军:我已经被时光腐败了
虽然多年来受着严重抑郁症的困挠,但骆以军的性格中始终有着可爱的一面,像个孩子似的。采访在他的酒店房间内进行,他索性光着脚,说到兴起还盘腿坐到了沙发上。
但是,烟不离手。即使拍照,他也习惯性地点支烟,放松一下有点僵硬的双臂与表情。这次带来的新书《遣悲怀》,封面上就是他腾云驾雾后的产物:一团烟雾。
与获得“红楼梦奖”的《西夏旅馆》那读起来有点拗口的长句不一样,《遣悲怀》好读很多。这是骆以军为纪念1995年自杀身亡的女作家邱妙津创作的。他俩是好朋友,同属“五年级生”(即内地的“60后”),都是通过文学奖制造出来的小说家,“我跟他是同一届,我是短篇的第二名,她是中篇的第二名。”
至今,骆以军还清晰地记得,领奖那天,邱妙津将家人都带来了,热热闹闹地拍照,“那时会有那种文人同辈看对方不顺眼(的想法)。我们那个年纪,总觉得灵魂应该是孤独的,碰到这种人群的场面应该是沉默的,比较像董启章那样。”
熟悉骆以军的人喜欢叫他“骆胖”,因为他现在很胖,但是年轻时他并不这样,而且现在他常常呱呱呱的,“那是我已经被时光腐败了。”
回忆当年,“我是非常的安静、沉默和害羞的,就像那个时候自杀的黄国峻,都是非常忧郁和沉默的,都没有办法和正常世界的人联系上。”那时候没有网络,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宿舍里读书,读福克纳,读前辈让他们读的书;看电影,看法国新浪潮、看意大利电影。所以,“邱妙津当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我们聚在一起也是很文艺青年那种的面谈。”
他还记得阳明山上的放映间,看伯格曼、看安哲罗普洛斯、看宫崎骏。看《柏林苍穹下》时,他突然就想站到风中抽烟,“我就是在追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庞大的世界,没有那么庞大的维度,没有网络打开来的世界。我觉得过了我们那个年代,不光是台湾,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阶段。”
在骆以军的小说启蒙上,张大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大春也是当时教他小说课的老师,因此他的小说创作起步便被人贴上了张大春的标签,“我们那一辈,张大春其实就是那个遮蔽天空的,或者是说引领我们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回头看第一本小说,还是觉得跟张大春完全不像。
说到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则充满了感激。那时候,他的创作处于低谷,差点放弃了,“当时环境很不好,我本来已经不想写了,如果没有一个支撑点很容易崩溃,自我瓦解掉。”是朱天心,跑到了他的家中,对着他说:你是这个世代最好的。所以,骆以军和朋友在一起时,“绝对是人渣废柴”,会乱讲话,“他们会跟我讲很多变态的事,我会和他们讲很多黄色笑话”。但是,在朱天文和朱天心面前,他“从来就是像小辈一样,这个并不是装模作样”。
董启章:我对怀旧没有兴趣
与骆以军完全不一样,董启章很安静、沉默,不善言辞。
他和骆以军一样都是“60后”。在见到真人前,董启章就已经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新人作家叫骆以军,“知道在台湾那边,也有人跟我差不多,开始从事文学这样的事。”他说,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感,“像遇见一个对手那样的感觉。”但是,与骆以军喜欢跟人PK不同,他“是比较正面的那种”。
董启章说自己的创作起步比较幸运。他读的是比较文学专业,读了很多作品,惊讶于那些好的作品的想象方式,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当然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只是觉得还可以,还有发展的空间。内心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表达。慢慢觉得这是一件自己有能力,也有很强的欲望去做的一件事。”
刚开始写的时候,他主要是写短篇,“这个跟香港的环境比较有关系。在香港写长篇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出版比较难,发表也比较难,因为这么长,没有地方可以给你连载。”
经老师推荐,他认识了《星岛日报》的副刊编辑,“当时有很好的一个机缘是,1992到1993年的时候,《星岛日报》有个文艺副刊,它的编辑很好,是一个在文坛里面比较有名的人,非常愿意让新人去发表作品。所以,最初我写的小说都在那里刊登出来。当时我还蛮兴奋的。”这样一个平台,“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能发表的动力是很重要的。”
书展期间,他来宣传的书其实已经是去年在内地出版的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他的“自然史三部曲”之一。小说中,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以“物”为题,这些物都能勾起大家的某一种集体记忆,比如收音机、蝴蝶饼与耳朵、电报/电话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