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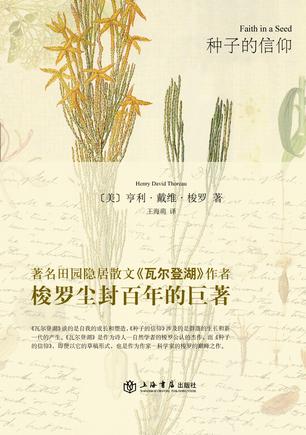 《种子的信仰》是一本寻根的书。天下有各式各样寻根的故事,而梭罗则将笔触回溯到自然界的根源。他把目光停留在微不足道的种子身上,通过追寻森林成长的轨迹,揭示了种子传播和生长的秘密。无论远足,还是写作,梭罗都是为了完成同一项根本的追求,即对世界本源的探索。 《种子的信仰》是一本寻根的书。天下有各式各样寻根的故事,而梭罗则将笔触回溯到自然界的根源。他把目光停留在微不足道的种子身上,通过追寻森林成长的轨迹,揭示了种子传播和生长的秘密。无论远足,还是写作,梭罗都是为了完成同一项根本的追求,即对世界本源的探索。
对世界本源的热情贯穿了19世纪的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是有力的明证。在《种子的信仰》里,梭罗不止一次引用《物种起源》以及多部欧洲科学著作,如《鸟类史》、《植物学》等。事实上,这股寻根探源的烈焰不仅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熊熊燃烧,也深深影响着同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人类学就是在19世纪萌芽的,而梭罗在文中也引用了皮克林的《人种及地理分布》,谈论文明人和野蛮人对种子分布的影响。同时代的小说家,如乔治·爱略特也注意到这股社会潮流,在《米德尔马契》这部长篇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希望发现所有神话起源的牧师和一个试图找出所有生命之源的医生。借用爱默生的话,这类探索的目的之一是证明“人类王国可以征服自然王国”,这给予了人类“一种统治权,这如今在他的梦想之外”。在此历史背景下,梭罗对种子的探索就并非仅仅出于热爱自然的本性,而是希望通过对细致的观察把握一门知识的秘密。因此,梭罗的研究态度首先是科学式的。在这本书里,他显示了惊人的细致与严谨。所有观察都有详细记录,观察的日期、植物的形态、动物的踪迹、地形地貌等等都有准确记载,而且这种记载往往持续若干年。可以说,康科德的自然界对梭罗而言是一个自足的文本,他如同最忠实的读者,竭力阐释着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大自然本身的变化。
然而,梭罗又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兴起就与他、爱默生及富勒的倡导息息相关。作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宣称存在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越于经验和科学之外,通过直觉可以得到把握。爱默生于183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自然》,在最后一章,他提出人是“沦为废墟的上帝”,而大自然则是他孤独的意识。因为人类创造力的丧失,自然冻结为一种象征形式,而人可以通过破解这些暗示逐渐恢复他丢失的能力。从这一论点出发,可以发现自然界不再只是物质,而是对人的思想具有一种救赎作用的生命存在。梭罗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这一主张身体力行。他在新英格兰群山中的无数次远足正是希望通过自然媒介,完成对人类内在神性的回归。
相对于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梭罗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充盈着一股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在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里,每种事物都在和其他事物交谈、回应,形成复杂的对话体系。如梭罗所言:“每棵树、每丛灌木、每棵草都把头昂扬在白雪之上,它们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结冰的外衣,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回应夏季的装扮。”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自我、自然以及大地循环的语言。在大自然中可居可游可写的生活对梭罗而言乃是一次自我发现的经历。他不仅是严格的记录员,也是自由的漫步者,他将自我铭刻在荒野之中,这已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如梭罗所言:“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主要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是生活在其间,不管它是好是坏。”上山下湖都是生命过程的实现,是最快乐的问与答。世俗意义上的家已不再重要,因为大地处处都是家。可惜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经历很陌生,农夫对他们的田园知之不多,只顾毁林赚钱。梭罗没有直接攻击这种实用主义,他只是静静地在林问行走、丈量、观察,将这场对话化为一场隐秘而私人的经验。这场持续的行走最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如果不是镇里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想用自己的事打扰读者们的注意力。”无论初衷如何,他的个人目的最终影响了其他人。
在梭罗于哈佛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美国学者》为题发表了演讲,吹响了美国文学独立精神的号角。他提出美国人“倾听欧洲显贵的缪斯已经太久了”,希望美国自由人“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要用自己的手工作……要说出自己的思想”。我们不知道梭罗是否聆听了爱默生的发言,但可以肯定,他比起同时代的人更好地履行了爱默生的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