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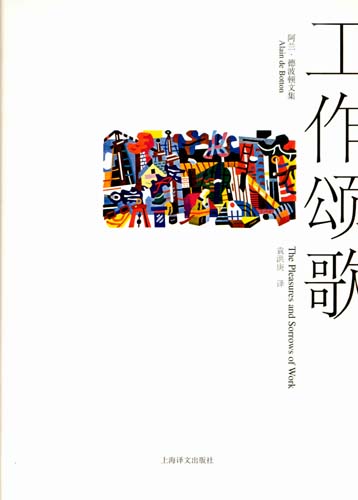 阿兰·德波顿说,他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六年前他的首度中国之行。那一年,他在京沪两地签名售书,还在北大和复旦亮了相,受到学子们追捧。他很意外自己在中国竟然能赢得那么多读者。 阿兰·德波顿说,他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六年前他的首度中国之行。那一年,他在京沪两地签名售书,还在北大和复旦亮了相,受到学子们追捧。他很意外自己在中国竟然能赢得那么多读者。
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引进出版了他的新作《工作颂歌》,冠以“2010年度最熨帖人们心灵的作品”称号,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入读剑桥大学只醉心于恋爱和创作
阿兰·德波顿于1969年生于瑞士,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8岁被送到伦敦念书,18岁入剑桥大学,通晓英、法、德、西班牙、拉丁等数种语言,喜欢旅游、购物和谈情说爱。
阿兰·德波顿自称,其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的失败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尽管剑桥贵为世界一流学府,但他对学校的课程却一点也不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基本致力于逃课、在图书馆消磨时光,父母在一家书店为他开设的账户令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疯狂购书。如今的年轻人怕是很少有能像他这么幸运的:念大学不是为了学位和日后求职谋生,读书只是为了“徜徉古今,和他喜欢的人神交”。
23岁那年,阿兰·德波顿发表处女作《爱情笔记》,大放异彩:该书虽号称是小说,但几乎谈不上情节和结构,通篇是男主角对自己恋爱经过的细腻体验,乃至于提升到了心理学与哲学的层面,被评论界称赞为“充满创意、处处机锋”。其后他又写了《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延续跨文体和知性的特征,“分析爱情不惜从柏拉图一直引证到马克思”,25岁即入围著名的法国费米娜奖。1997年出版的《拥抱逝水年华》更是让他名声大噪,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性格、癖好、为人处世之道,他把高高在上的普鲁斯特和他那部让无数人费解的《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人生指南。此后相继出版的《哲学的慰藉》、《旅行的艺术》、《身份的焦虑》,都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除聪明、博学外,阿兰·德波顿似乎还记忆力惊人,书中信手拈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譬如他知道尼采为父亲设立的墓碑上镌刻的圣经语录,知道普鲁斯特一天的食谱,知道路易十六为大卫的名画《贺拉斯之誓》开出的价钱……
新作让其身陷“毒舌门”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位英伦才子欣赏有加,有人讥讽他“身上有一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更糟糕的是,他的新作《工作颂歌》反响不及前作,而阿兰·德波顿对于批评声的反应之过激,大违其一向给人的温和、理智印象,令很多人惊诧。
事情的源起是,《工作颂歌》在美国上市后,《纽约时报书评》发表了书评人卡雷布·克雷恩的一篇评论,质疑德波顿的写法和观点,指责德波顿在书中“肆意放纵自己”。翌日克雷恩的博客上就出现了署名德波顿的激动留言,称这篇书评完全出于“近乎变态的想要出口伤人的疯狂欲望”,甚至“狠毒”地对克雷恩说,“我到死都会记恨你的,祝你事业吃了一堑又一堑,我会兴致勃勃幸灾乐祸地在一旁看着。”在文坛引发轩然大波。此后尽管阿兰·德波顿也表示说挺后悔当时那么按捺不住,但他仍为自己的新作辩护说,他的写作动机不过是为了照亮一些不为人充分认识的工作活动,“那也是我们作家的职责”,而克雷恩写的书评几乎是故意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反而扭曲了他的用意,他强调说,“书评人应当具备公正的道德责任感”。
我们国内的评论家也不怎么待见这部作品,作家、书评人小宝就声称,较之过往作品,《工作颂歌》明显“沉浸在一种浅薄的快乐中”,甚至有些尖刻地说,这本书或许是德波顿婚后为了补贴家用、纯粹冲着畅销草率写成的。
对话阿兰·德波顿:“我一直按自己的方式安排文字”
广州日报:最近您的新作《工作颂歌》在中国出版了,您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关于工作的书?
阿兰·德波顿:弗洛伊德曾经有一句名言说,快乐生活需要两样东西,爱和工作。我已经写了很多关于“爱”的文字,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工作”也算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很感兴趣。
广州日报:您把工作写成“颂歌”,这似乎跟一般人把工作视为负担的想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