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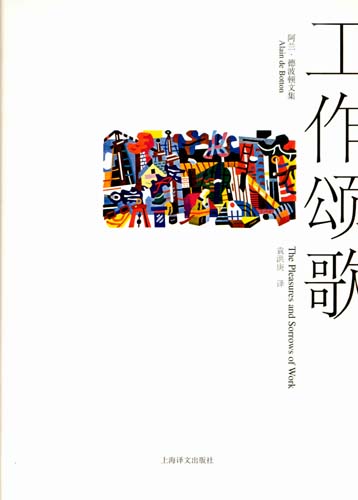 阿兰·德波顿“来到”中国与几个喜欢他的年轻人有关。那是六七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几个“70后”编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这位英伦才子的作品。用策划者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冯涛的话来说:“德波顿的东西好读又不失趣味,读起来有一种自由通畅的感觉。” 阿兰·德波顿“来到”中国与几个喜欢他的年轻人有关。那是六七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几个“70后”编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这位英伦才子的作品。用策划者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冯涛的话来说:“德波顿的东西好读又不失趣味,读起来有一种自由通畅的感觉。”
其实,德波顿的处女作《爱情笔记》中译本,之前曾出现在国内一套介绍国外最新小说的译丛中,但如一粒石子落入大海,很快无声无息。为了把德波顿全面介绍到中国,冯涛、孟丽等几个年轻编辑花了很多心思,终于在2004年4月推出了囊括德波顿当时所有作品的6册文集:《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惊世之作《拥抱逝水年华》,以及《哲学的慰藉》和《旅行的艺术》。
2009年他们再次出版德波顿的新版文集时,又增加了德波顿后来创作的《身份的焦虑》、《幸福的建筑》、《工作颂歌》。
德波顿约等于英国余秋雨
仅仅一个“英伦才子”的介绍,使德波顿在中国读者面前仍显得面容模糊,甚至因为他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让人们谈起他时更是有些混乱。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冯涛打了一个自己也认为不太恰当的比方,但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这位英伦才子。“我们几个同事私下开玩笑说,德波顿有点像英国的余秋雨,但他的学养比余秋雨更整齐。”冯涛强调,这个比方只能作为读者的大约参考,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12岁时全家移居伦敦,18岁入剑桥大学。他的学养是纯欧陆式的,德波顿喜欢的是十七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如蒙田、拉罗什福科等。德波顿曾给自己“定位”为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德波顿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
2004年5月,德波顿曾受邀访华,当时冯涛作为陪同之一,在各项活动间隙跟德波顿有过一些交流。“德波顿在生活中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nice’得不得了。”冯涛说,当时,他曾没话找话问起他以后的写作计划,德波顿说打算写一本有关建筑的书(即后来的《幸福的建筑》一书)。于是冯涛继续问德波顿对上海和北京的建筑做何评价,德波顿回答挺喜欢上海现代化的高楼,然后话锋一转说他很不喜欢伦敦二战后建的很多廉价丑陋的房屋。
几年后,冯涛在翻译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时,才明白他当初“不过是客气话”,德波顿根本不喜欢如今这些毫无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水泥森林。译完全书后冯涛还曾心生一点小遗憾:德波顿怎么在书中对中国之行中看到的中国建筑不置一词呢?也许他是行程太过匆忙,来不及细细考量周遭的建筑细节,再则,显见的也是他对如今的中国建筑不太满意吧。跟自己客气一句没什么,像“立言”这样的大事哪能随便敷衍?
冯涛还告诉记者,当时因为行程安排得较满,有一日深夜11点多,德波顿还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德波顿提出是否可以回绝采访,冯涛等人虽然觉得很抱歉,但确实有些难办。德波顿于是同意继续接受采访,自始至终都非常耐心、礼貌地倾听,哪怕是被问了许多次的问题,他都会非常清楚认真地回答,举手投足都非常绅士。
德波顿是个天才,也是通才
在冯涛看来,德波顿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和通才,讨论的主题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用自己的著作打通了诸多领域:爱情、文学、哲学、旅行、人对自己的认识、建筑、工作等等。每一次写作,德波顿都要做许多功课。不像国内的一些学者,容易犯“井底之蛙”的错误,有一点小见解就以为找到真谛了。若再找更多的书来读,才发现那么一点小东西早已经被别人表达过许多遍了。
冯涛翻译了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他以此为例说,《幸福的建筑》绝非一本“西方建筑××讲”或是“××家居廊”,也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西方建筑史,它或是教你如何欣赏建筑的鉴赏手册,但不是你可以拿来指导你新家装修的实用指南。德波顿想解决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即:建筑对人到底有何重要意义,跟人的幸福又有什么相干?他探讨建筑问题的角度与做出的解答会整个颠覆你日常接受的那些有关建筑的陈词滥调,会促你从根本上改变对建筑进而对于人生和幸福的既定态度与追求。
冯涛一直认为,读德波顿的作品,能够获得一种被打通的感觉,自由,通畅,毫无晦涩之感。德波顿自己也曾说过:“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当然难免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写让人看得懂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