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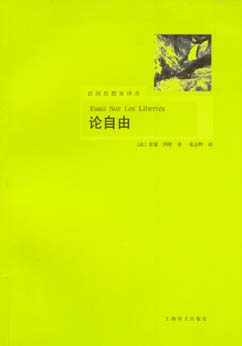 在阿隆看来,要实现自由的各种要求,首先要慎重地设计民主的程序,既要避免出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暴政”,也要防止哈耶克倡导的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 在阿隆看来,要实现自由的各种要求,首先要慎重地设计民主的程序,既要避免出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暴政”,也要防止哈耶克倡导的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
“自由”可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记得前年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我曾利用寒假乘火车、换长途汽车,一路从弗吉尼亚考察到纽约。由于正处于反恐战争时期,纽约各处的气氛紧张、凝重。在作为美国自由经济象征的原世界贸易双塔废墟附近,人们只能隔着玻璃窗观看,而且禁止拍照。不远处,作为美国政治自由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也在“9.11”之后被封闭,游客们只能乘渡轮“欣赏”。不过,这种紧张和凝重远不及随后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来得猛烈和彻底。如果说“反恐战争”只是耗费了“三万亿美元”,那么金融危机却动摇了美国的国基,有消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了”。要求“清算”美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就有高官提议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巴西、俄罗斯等国决定抛售美元,等等。就连前苏联的终结者戈尔巴乔夫,这个“冷战”最大的失败者,也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呼吁美国也要进行前苏联式的改革。历史走到这一步,我不禁联想起福山十多年前写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显然,历史已经“证实”了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并非“自由”的唯一模式。当然,历史还在继续演变,不断会证实或否证我们的判断,谁都不是“笑到最后的人”。不过,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一直想追问的是:美国自由模式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正好,我手头有一本近年迻译过来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为我澄清疑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讨论平台。说起雷蒙·阿隆,国人应该并不陌生,他的学术代表作《社会学的主要思潮》在三十多年前就被译成中文,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可惜的是,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历史哲学引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都未迻译过来,国人难窥其思想的全貌。好在《论自由》一书虽然简略,却颇能反映阿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书名上看,阿隆对“自由”的讨论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论自由》的原文是“Essai sur les libertes”,意为“论复数的自由”,或“论多重自由”。在阿隆看来,自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从自由的内容方面来看,自由应分为形式的自由和实际的自由,前者又可称为政治自由,包括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而后者也称为经济自由。若是从自由的实现角度看,自由又是与人的能力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自由的内容方面。阿隆是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分歧入手的。托克维尔虽然出身贵族家庭,对贵族自由一直情有独钟,但是并不保守,他敏锐地发现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平等已是不可逆转之势,所有人的社会状况(或条件)完全平等化,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不依附他人的;换言之,传统贵族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完全解体,转变成由众多如原子般的独立个人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本质上已不仅仅是什么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而是一种社会生存状况。不过,这种社会生存状况如没有制度制衡,就会造成各种民主的暴政,即“大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托克维尔非常强调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注重政治与法律制度的设计要以保护个人的政治自由为前提。
马克思的出身与经历却不同。虽然早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就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成熟期却晚于托克维尔,而是处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因此,马克思对工业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现象感受很深,认为托克维尔等人倡导的“政治自由”只是“形式自由”,并不能直接带来“实际的自由”,即免于贫困的经济自由。可以说,马克思第一个注意到了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之间的差别。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中化要求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又由于无产阶级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资产阶级只是非法占有剩余价值的寄生虫,所以“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避免。而革命胜利后,又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在现实政治中,特别是在前苏联的政治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演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技术统治,不仅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由于反对个人自由,也就在经济和管理上缺乏活力和创新。在阿隆看来,马克思的理想——“自由人的联合体”——不仅未能实现,而且“比美国的梦想和当今美国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第88页)。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形式自由,即公民在政治舞台上选择其代表、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自由,在西方继续存在,但在苏维埃制度中已不复存在”(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