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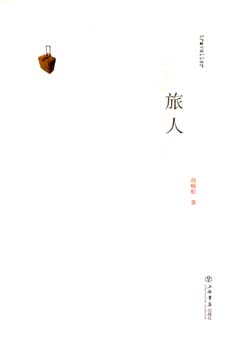 胡晴舫的《旅人》,讲的是关于旅行以及旅行的人,但更要紧的,是关于旅行者流离的眼睛所看见的别人与自己。 胡晴舫的《旅人》,讲的是关于旅行以及旅行的人,但更要紧的,是关于旅行者流离的眼睛所看见的别人与自己。
旅行者离开家乡的时候,正确的说,是他(她)第一次离家的时候,他(她)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他(她)昕有的,只是“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些想象,或者来自书本(也就是所谓的“知识”),或者来自于转述(但奇怪的,这时候我们就改叫它做“传言”了)。
一旦出门远行,他(她)的“想象”就要和“真实”面对面,产生一种交锋、对质,更产生一种演化观点,从而成为一种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来。那个过程,也许我可以称它是“当世界观与真实世界相遇”……
因为你对前方的世界一无所知,你所熟知的,其实是自己原有的世界,所以当你背起行囊勇敢向前之际,你其实是个“带着家乡去旅行”的人。
我本来以为我是个轻便的旅人,只带了一点换洗衣裤(我还带了路上可以丢弃的旧袜子)、刮胡刀和牙刷,以及一本旅行地的导游书;但事实上,我带着出门的远比我知道的为多,我带了一整箱“偏见”和“旧习”,以及一双被自己来历禁锢的眼睛……
“嘿,这里的茄子竟然是圆的。”
“在日本,菜是冷的,饭是温的,鱼是生的。”
“德国的女人胸脯大到她们拍面包屑时,是拍胸部而不是拍腿上。”
“在美国中西部,你可以开一天的车子看不见另一辆车子,景色也完全没变,一片接一片的玉米田。”
“物不自异”,这些奇风异俗,其奇其异,都是通过观看者的“自身对照”得来的,可见我们虽然来到“异乡”,但我们背负着一整个家乡的“监狱”,我们根本没有离开家呀。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旅行?为什么又给予旅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么高的学习评价?
可能是因为到了“回家”的时候,旅行者又“变”了,他(她)变得和原来不太一样,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未察觉。回来的旅行者,眼睛变得不太一样,他(她)竟然不太适应他(她)原来已经居住多年的家乡,他看到很多不顺眼的事,忍不住把一些他乡的事搬出来说……
“穿过中越边境,你就发现越南人是爱干净的,中国人是不讲卫生的。”
“你看看德圉人,半夜无人时,他也要停下来等红灯。” “那是一个真正法治社会的表现。”
“在法国,每位工人也都能讲一两本他喜爱的书。而在意大利,卖肉的屠夫还能和你背诵但丁呢。”
你旅行,你变了,你“带着异乡回故里”了,你已经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
奇怪的是,出国时你无法摆脱你的家乡,回来时你却无法融入你的故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胡晴舫在书中说:“旅人带着他的偏见赶路,有些旧偏见被印证,成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见。经由旅人的闯入,则影响了没有离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或,另一面的偏见。”
我仍然可以说,这些偏见的否定和再肯定,是一种“进步”。回来的你“否定”原来的你,但回来的你“包含”原来的你,如同果实是开花的否定形式,但果实是包含开花的过程的,你不能绕过它。
到了这里,我们也才探触到一点点旅行的真相,而且我们还只用了两个数学变量,家乡和他乡;如果家乡和他乡都变成“复数”,那又如何呢?例如胡晴舫书中开宗明义说的“我总是在路上”,一个场景换过一个场景,一个思考基础换过另一个思考基础,如果“时差”是此地到彼地的“生理时间”调适现象,总在飞行的人又要以哪一个地点成为他(她)“时差”的基准点呢?
或者,我另一个朋友的故事,她生在香港,先到台湾读大学,又到美国读研究所,回到香港工作,然后又嫁到丹麦去,一生充满移动和困惑,她究竟要如何看待自己?在台湾读书,她是个讲话有口音的香港人;回香港工作,她看香港不顺眼,朋友觉得她已经变成台湾人了;嫁到丹麦,她开始怀念在香港成长的一切。这就是旅行无止境的辩证,“地基”不断移动的人,多了许多看世界的机会,但也失去站在某个“立场”的权利。
观看者如此,被观看者又如何呢?早期读西方旅行文学,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因为,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有时候是难堪的。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落后怪奇、不适人居的蛮荒之地,有时候正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被迫看到另一面镜子里衣着褴褛的自己,不免也有点难堪,但对居高临下、趾高气昂的闯入者、偷窥者,也有一些不满意和不谅解。有时候也不免学阿Q的口吻说:“我们家从前,比你们阔多了。”
你看看我,本来要谈胡晴舫的书,却拉杂谈到爪哇国去了。但这正是胡晴舫《旅人》的撩拨力量,她永无止境移动观点的旅人之书,刺激你的思考停不下来。它本身是一本反省旅行意义及旅行途中所见的书,你不可能坐在那里,呆呆读着这本书,你的思绪早已动身,前往你不曾造访之地。你,和她一样,也想要苦苦追问,一切关于“行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