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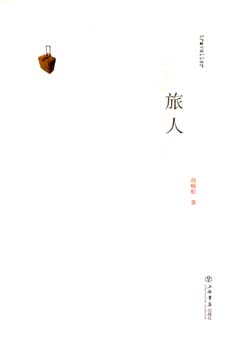 胡晴舫新书《旅人》(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以另类的文化眼光看旅行、看人生,颇有意味。本文摘编自该书。 胡晴舫新书《旅人》(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以另类的文化眼光看旅行、看人生,颇有意味。本文摘编自该书。
这是一个旅游过剩的时代,他们说。旅游变得太轻易、太舒适、太频繁、太理所当然,有智之士出来宣告旅行的死亡。
而文化,变成旅人最新的救赎。
当再没有新大陆或新岛屿可以让旅人以自己名字命名,发掘星球的权力又只是属于少数菁英科学家的昂贵特权时,我们开始讨论文化。生态之旅、文化深度旅游、民俗之旅等。新概念的提出为已经山穷水尽的二十一世纪旅游寻新的生路。
你可以:去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生活三个月,包含机票大约美金三千元;前往德国南部巴伐利亚村落消磨一个夏天,团费只要新台币七万五千元;到英国牛津大学暑期进修,注册费连生活费大概人民币七万五;上中国河南少林寺打拳,一个月六百美金;去纽约东村的戏剧工作坊练肢体,两个月课程,学费美金三千元;窝在日本京都的温泉旅馆,着和服穿木屐,一个晚上一万五千日币。
你也可以:照切·瓦格拉当年骑机车的路线认识拉丁美洲;走访海明威在巴黎厮混的地点;依亚历山大大帝扩展帝国版图时的痕迹去游马其顿;躺在南中国海的一处小岛,听着村上春树小说里提过的爵士乐。
在现代旅游系统中,文化经验是一种商品。文化,一如旅人脚上所踩着的运动鞋,可以被复制、量产,拿出来公开展示,标上价钱,贩卖给任何遐想异国情趣的人。怀旧的旅人,伤感追忆过去的黄金时代,任何事物冠上“文化”二字,必定无价、高贵、独特,不可亵渎。但,正如所有传说中的黄金时代,旅人的黄金年代也已经逝去,迟来的现代旅人只能面对堕落后的世界,学会认知如今的文化之旅如何成为利维·斯特劳斯最大的梦魇。
机械时代里,文化经验能够一再复制。曾经,文化需要一整个民族及许多世代的生命投资,经过时间的缓慢演进,经验分享与传承,现代的资本与技术使得文化情境的重现变得轻易快速,而且能经得起大量生产。
这是为什么每一个游客到了纽约一定要去百老汇看场音乐剧,在巴黎就要在香榭大道的露天咖啡座喝上一杯咖啡,在日本箱根必要泡一趟温泉,去了罗马就在许愿池丢一个铜板。这种复制的行为,本身已是一种文化仪式。仿佛没有完成这项仪式,旅行就不曾完整。
透过旅行这项行为,造成私有化的现象。纽约不再是纽约,巴黎不再是巴黎,东京不再是东京,而是“我的”纽约,“我的”巴黎,“我的”东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旅行书写在这个时代大量地被制造,也前所未有地严重贬值。
旅游照片,渐渐如同婚纱照片和新生儿相片,本来应该具有珍贵特质,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却沦落与其它在机械时代被大量生产的物品一样,一旦多了,就不是那么稀罕。所以,当那些婚纱照、新生儿、旅游相片被拿出来展示时,当事人津津有味、活色生香地高谈阔论,而访客只是礼貌性忍耐着,不时偷瞄腕上的手表,找机会离开。
旅行,这个概念与所有的不寻常冒险连接在一起的浪漫,不再遥远,如今,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享用。
经验与个体生命的单独存在紧密结合。每一个存在都独一无二,每一趟旅行也都无法取代。重点,不是米兰之行,重点是“我的米兰之行”。当时,米兰街道的空气味道都特别地与往年不同;“我”还记得,雨水的味道是甜的。
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到了罗马的老实泉前,将她的手羞怯地放进狮口中,百分之八十的可能,她想到奥黛丽·赫本和《罗马假日》。在那一刻,她就是奥黛丽·赫本,她就是公主。
机械的复制能力,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读过听来的故事中的主角。文化的瑰丽色彩,增添旅游故事的价值性。
遗感的是,机械复制的文化之旅,终究要像一张梵高《向日葵》画作的明信片,一只希腊街头小贩叫卖的仿古单耳陶壶,一把现代印度人做出来的古代西塔琴,买的人欢天喜地,但,总有人会跑出来告诉你,那些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价值,它们的唯一用途就是证明你那无药可救的品位,及大众商业系统的确无所不在。
而文化跟旅人之间的关系,在机械时代里注定是重复的、缺乏创意的、虚假的、廉价的,以及媚俗的。唯一庆幸的是,告诉你这项事实的人,也逃不过媚俗的命运。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共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