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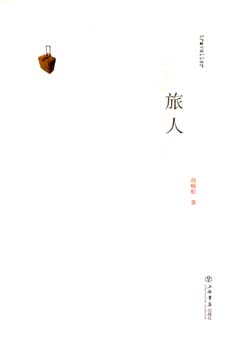 一开始撰写这些文章,一些读者以为我真是太政治不正确,又太愤世嫉俗了。因为,我谈到了疆界和离开,表达对时下流行旅行观念的质疑,也悲观地认为文化在旅游市场上逐渐橱窗化,成为一种媚俗的商品,虽然我自个儿一点也不反对商业化这件事。 一开始撰写这些文章,一些读者以为我真是太政治不正确,又太愤世嫉俗了。因为,我谈到了疆界和离开,表达对时下流行旅行观念的质疑,也悲观地认为文化在旅游市场上逐渐橱窗化,成为一种媚俗的商品,虽然我自个儿一点也不反对商业化这件事。
关于这些评语,我虽有点被误解的难过,却很习惯。习惯到我自己都不习惯的地步。我向来以为自己是“政治太正确”了。我受教育的历程、就读的学校、成长的社会环境、阅读的书籍、交往的朋友,给了我太多这方面的训练,无形中成了束缚,很多话在出口之前,我的大脑已经反复否定再否定,因为,我很清楚,那是不符合主流思想文化的一种说法。我以为,政治正确是我个人思考深度上的一大限制。
然后,我毅然决然展开我个人想象中的旅程。因为我以为,所谓的“政治正确”在现代社会铺上了一层思想地基。从这个思想地基,人类可以如何继续增建更精雅考究的建筑,是势必要往前跨出的一步。而,如何真正在现实中实践这些激情的思考,也是非常艰难却必定要试图去做的工作。单就思想成长来说,就算一些观点,目前来说是政治正确的,我们能怎么挑战自己,再往前思辩,不以目前的思想高度为满足,我们还能怎么样再调整我们观看世界的角度,我们还能如何再提出充满原创性的诠释,是每一个当代人对文明的义务。
因为,今日的“政治正确”,是先人挑战当时的“政治正确”,累积新思想而成的。如果伽利略不挑战当时的教廷,如果当时人民不质疑贵族的特权合理性,如果女人一直满足于自己是第二性的说法,那么,今日我们仍活在一个封建天下,依旧相信地球是一个四方形,无限制的漫游将触及边缘而掉入万丈炼狱,而身为一个女性的我,大概还裹着小脚,也不可能出门旅行,还有机会坐在电脑前写作。这段从A到B、从B再进到C、C之后还要前往D……的不断文明过程,是我个人非常好奇、渴望学习而希望探索的。
是的,这就是旅人的精神。
世界如此大,旅人不会满足只停驻于一个城市,他总是还想再往前走,试图拜访一些从来不曾亲身进入的城市,尽量在一座高山之后再登上后面那一座高山,在地图上画出来或没画出来的地方寻找一条河流顺流而下。他充满热情,无知却勇敢,为未知所吸引,准备以各种方式拥抱这个世界为他提供的任何一项惊奇。任何一项。
旅人相信,每一个新的立足点,都能带来新的视野。在我那小小宇宙之中已经理解的事物知识之后,我依然渴望被冲击、被震撼、被激动、被感动。
在抵达脑海中所设定的目的地之前,旅人永远马不停蹄。
如此动机驱使我在一些似乎理所当然的既定知识面前,像一头固执甚至有些愚蠢的山羊,即使知道对面是一面坚硬的石墙,仍大胆用我头上的山羊角硬生生去撞击。
一个新世纪的旅人,注定要在一个已经过度被解释、过度被观看、过度被探索的世界中出发。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旧旅人知识经验,挤在已经够拥簇精彩的思想大厅里,新旅人仍奢侈地冀望自己能拥有看见新世界的幸运。
旅行迄今,我还只是在重复前代旅人所走过的路径。但,我把情势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无论我能否安全抵达我的目的地,我都已经回不去了。像一个离出发地太远的旅人,一路走来的旅途风光开启了我的眼睛,旅途上发生的事情翻转了我的思想。情愿不情愿,我都已被动或主动地受过一些洗礼。我看待事物的方法,永远不会再是留在原地的我的天真目光。我仍然相信我从前相信的一些道理,但是,我试图接近这些事物的方法将比过去更深沉复杂。
见过撒旦的人,或许因之堕落失足,或许不改其志,然而,无疑地,他都将对上帝形成一套新的看法。
二十二岁的达尔文跟随英军海军舰艇“小猎犬号”环绕世界一周,四年后回到英格兰,达尔文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从前乖乖站在圣经的面前,接受上帝花了六天创造世界而一场大洪水曾经摧毁世界只有诺亚方舟保存的动物活下来的说法。他注定要问那个所有人类都问过的一句话:“我从哪里来?”且,使用他自己的方式,就像哲学家透过哲学、生物学家透过基因、神学家透过神学、文学家透过文学、艺术家透过艺术,去调查他认为的真相。
旅行勾起旅人想要进一步了解世界的欲望。
如米兰·昆德拉描述的,有时候,世界会像一幅美丽的画突然从中间裂开一条缝隙,透过这条裂痕,你见到,有另一个世界其实存在于你眼前这个世界的后面。你平时看不见,也丝毫意识不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因为眼前这个表面世界一向是如此平整稳定,完美无瑕,占满你望出去的视野。可是,那条丑恶吓人的裂缝破坏了表面世界的完好。透露了你所不曾注意的讯息。它让你见识了你以往完全不可能想象你会见到的景象。
它证明了你所存在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你的观点不是唯一的观点。你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而你一直安心倚靠的知识其实是可怜而狭隘的。
而每一个旅人都是不甘受限于那些既定游戏规则的人类,时时渴盼从熟固僵化的环境抽身,总有一天,都要搭上自己的“小猎犬号”,扬帆出航,去发展自己对世界的一套解释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