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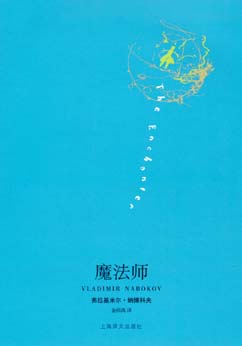 7月的一天,魔法师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一个穿旱冰鞋的12岁的小女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深深吸引了魔法师。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个小女孩,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个女孩后来跟着母亲的朋友离开了。 7月的一天,魔法师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一个穿旱冰鞋的12岁的小女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深深吸引了魔法师。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个小女孩,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个女孩后来跟着母亲的朋友离开了。
为了再一次见到这个女孩,他绞尽脑汁想着把女孩留在身边的办法。他开始一步步地接近女孩的母亲,不久便与她结婚了。婚礼时女孩回来,他非常想把女孩留在身边,然而这个计划被女孩的母亲否决了,婚礼后女孩再一次离开。此后,他不停地计划着怎样让女孩再回到自己的身边,他甚至想过毒死自己的妻子。后来妻子病死,他坚决要求让女孩跟他一起生活,想带着女孩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他们在一个旅馆里投宿,由于当地正在举行花展,旅馆房间紧缺,他跟女孩住在了一个只有一张双人床的房间。当夜,女孩熟睡后,他开始侵犯女孩的身体,结果女孩从睡梦中惊醒,尖叫起来。他跑了出去,冲向了正从山坡上驶来卡车,他死了,摆脱了这个疯狂的世界,一切都结束了。
与纳博科夫的其他某些作品一样,《魔法师》是关于疯人的头脑所看到的疯狂的研究。书中充满了魔法师的幻想,到处是他的精神活动脉络,他的计划、方案,他的梦呓般的念头。他时而清醒,有着疯子式的的机警;时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迷糊不清。与其说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乱伦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犯罪过程的心理记录。
一般的精神异常,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心理上的,都是滋养纳博科夫艺术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源泉。小说主人公的变态与异常——像后来的一部新作和一个不同背景下的亨伯特的犯罪恋童癖;像《绝望》中的赫尔曼的杀人妄想——就是纳博科夫选择用来创作虚构的重新结合的许多主题之一。纳博科夫在他的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打斗》最后一句话中写道:“也许至关重要的,根本就不是人的痛苦与喜悦,而是落在活人身体上的影和光的变幻,集合在一起的琐事的和谐……而且是以一种独一无二和无法模仿的方式。”
尽管这个魔法师是一个罪恶的变戏法的人,但是他也部分地生活在一个着了魔的世界里。不管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疯子,他从特殊而诗意的角度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疯子国王——让人产生瞬息即逝的联想,记起其他的纳博科夫式的国王,而这个国王同时又有几分像好色的李尔王的命运,与他的“小科蒂丽娅”一起住在海边童话般的隐居地,而瞬息之间在他的想象中她便成了一个被天真地热爱着的女儿。但是与往常一样,父爱又迅速变成了邪恶,他的性格中兽性一面陷入了恋童癖的幻想,并且表现得如此强烈。
纳博科夫否认自己的创作有政治或道德的目的,因为对他来说,“艺术的创造蕴含着比生活现实更多的真实”。他认为艺术最了不起的境界应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所以他的作品致力于用语言制造扑朔迷离的时空迷宫,制造个人的有别于“早已界定”的生活与现实,显示出一种华美玄奥新奇的风格。
《魔法师》被纳博科夫视作《洛丽塔》的前篇,预示了《洛丽塔》“着魔的猎人”的主题。在小说中,纳博科夫把“魔法师”设定为一个好色的中年男子。《魔法师》的情节和《洛丽塔》有相似之处,但魔法师用魔法把欲望变成了童话般的梦,从而创造了和《洛丽塔》截然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