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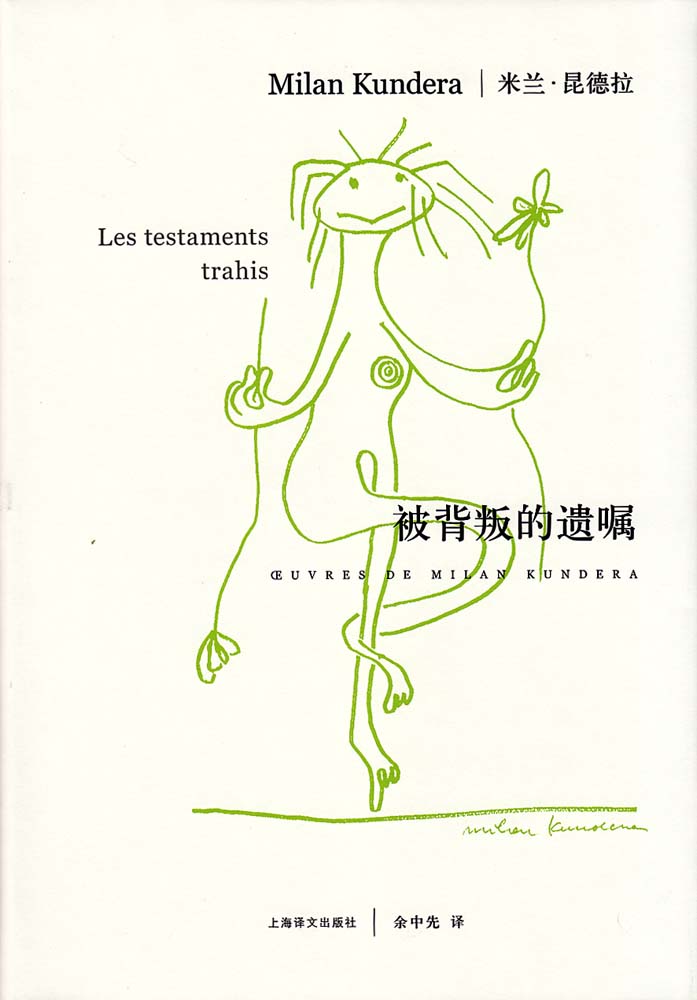 编者按 编者按
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近日出炉,加拿大女作家门罗摘得桂冠。有人欢欣,有人失落。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创立以来,已有百余人获此殊荣。然而,世界文坛群星闪耀,诺奖难免挂一漏万。总有一些大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对面不相逢”。此时此刻,诺奖像是一种提醒,让我们缅怀那些闪耀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的“无冕之王”们。
20世纪的文学史证明,已有不少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行列。但是,正如任何一种奖项都无法做到绝对公正和恰如其分一样,评选委员会也遗漏了不少堪称世界一流的作家,而将评选的标准和尺度倾斜给了某些相对比较平庸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任何一种奖项一样,都很难达到绝对的公正。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开始的100多年里,那份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固然有泰戈尔、罗曼·罗兰、萧伯纳等光辉灿烂的名字,但也出现了不少遗珠之憾。
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些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使它遭到了甚为激烈的批评和责难。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卡夫卡、左拉、高尔基……大师们作品的光辉并未因为获诺贝尔奖而有丝毫的减损,反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因此而受到了质疑。
保守主义者的“理想”
诺贝尔终生对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本人也写下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剧本,他非常推崇浪漫主义文学,尤其喜爱雪莱的诗歌,熟悉这位诗人的作品几乎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无疑,雪莱身上那歌颂云雀、呼唤西风的理想主义色彩深刻地影响了诺贝尔对文学的看法。故此,他在遗嘱中留下了关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要求和“最杰出的作品”的理解,正是凭借着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但是,在最初的10年中,以沃尔森为代表的瑞典文学院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由于他们保守的道德趣味和审美习惯,对“理想主义”狭隘的理解,剔除了相当一批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
保守的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使得他们在第一年度否决了左拉,在第二年度否决了托尔斯泰,前者被认为他的创作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后者被否定的理由是他“有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和“带有消极的禁欲主义”成分。
或许是处于摸索阶段的缘故,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最初10年的表现并非是尽如人意的,他们所作出的某些决定,有时甚至是与诺贝尔生前的言行相悖离的。事实上,诺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的怀疑论者,并且,恰在这一点上,他与托尔斯泰和哈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鸣。
中立政策下的无奈平庸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文学评选中也不由自主地奉行了一种“中立国”的政策。他们对诺贝尔遗嘱中的和平意愿理解为“首先要防止采取任何支持或反对的民族主义立场”,鉴于当时极少数的作家能够超然于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文学的桂冠自然就落到了某些政治立场中立、其创作成就相对比较平庸的一批作家身上。
同时,评奖委员会在美学趣味上,则由前阶段的保守,转向了大众的立场,开始偏爱简单性和通俗性,希望奖励能够“一目了然”地读懂的作品,这使他们拒绝了瓦雷里、霍夫曼斯塔尔、克洛岱尔、维多夫罗、普鲁斯特、乔伊斯等孤高、晦涩的现代主义诗人和作家,他们声称“为了普通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现代派诗歌和以此为目标的一小部分人拒之门外。
文学领域的“风险投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使奖金的授予囊括文学领域里最优秀的作家。因为,作家和研究人员的质量实际上根本不能定量分析。他们就发展出了一套“实用主义”的遴选原则,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投资和赌注。于是,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倾向于奖励一部新作而非对某个作家终生进行盖棺定论。
评奖委员会的这种转向是富于建设性意义的,它可以帮助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但缺乏创新所必需的物质支撑的作家继续从事创新的工作,可以让一部分相当有潜质但长期被忽视的文学趋向受到重视和支持。确实,对于那些已经建立了“世界声誉”的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除了能够增加他的遗产以外,没有其他的用途。
这种文学领域的“风险投资”包含了很大的风险,它不能保证获奖者最终肯定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师的行列。但是,比起那种没有任何创造的平庸的失误来说,由此而出现的失误或许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失误。
下面这份名单上的人虽然没得诺奖,但历史已经给了他们最公正的评价。因为,作家并不会因得诺奖而伟大,但会因作品而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