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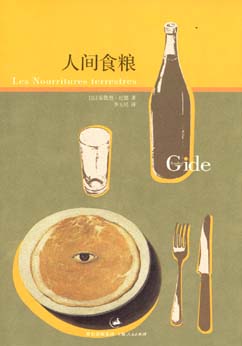 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通常所说的迷宫,如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克里特迷宫,人进去就迷路,走不出来,困死其中。忒修斯是个幸运者,他闯进迷宫,杀死了牛头怪弥洛陶斯,多亏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才最终走出来。
然而,纪德的迷宫则不同,它不仅迷人,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点: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这迷宫的一扇窄门,他的许多朋友,他的绝大部分读者,从窄门挤进去,仅仅看到一个小小的空间,只好带着同样的疑惑又退出来。他的几乎所有敌人,有时连窄门都闯不进,只好站在门口大骂一通。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为友为敌,还是普通读者,大都未能一识纪德迷宫的真面目,未能找见连通这些作品的暗道密室。克里特迷宫中有牛头怪,纪德迷宫中有什么呢?
纪德迷宫中,有的正是纪德本人。
换言之,纪德笔下的神话人物忒修斯进入的真正迷宫,正是纪德本人。
纪德通过忒修斯的口承认:
“我始终是大地的孩子,相信人不管如何,也不管如你判断的有多大污点,总应玩一下手中掌握的牌。”
纵观纪德的一生,他就是一直在玩手中掌握的牌,玩人生这副牌。临了他说:“我不枉此生……我的命运圆满完成。”(《(忒修斯)》
命运圆满完成:忒修斯身后留下了雅典城,纪德身后则留下由他的著作和一生经历构建的迷 宫,一个供现代人游赏,尤其思索的地方。
然而,纪德玩人生这副牌,根本不按即定的规则。他说:“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这是他的人生宣言,他向家庭和整个社会宣布,他的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只因人人都遵循的规则,在他看来就是生活在虚假之中。
首先他意识到,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天性,长此下去,他势 必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完人”,即符合传统道德而天性泯灭的人。
当时文坛活跃的两大流派中,象征派诗人如马拉美等,完全“背向生活”,而天主教派作家如 波德莱尔等,则以一种宗教的情绪憎恨生活。更多的无聊文人身负的使命,就是掩饰生活。
于是,他提出“做我们自己”,拒绝家庭和社会的一切束缚。他花费毕生精力去争取自由, 仅仅为了让天性自由地发展,享受真正的生活。
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放纵天性,“做我们自己”就是“倒行逆施”。纪德深知,必须同虚 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走一条逆行的人生之路,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
他写《人间食粮》,就是“要把文学重新投入人生这个源泉中去”(《纪德谈话录》)。为此 目的,他还相继发表了《乌连之旅》、《背德者》、《浪子归来》、《如果种子不死》等。尤其《人间食粮》和《如果种子不死》,前者是追求感官快乐的宣言书,后者是他同传统 教育的一次彻底清算。
纪德开着自制的动力十足的新车,一辆辆开进社会,但是逆向行驶,横冲直撞,撞倒了路标 路牌,撞破了许多路障。有人不禁惊呼,纪德是道德的“颠覆者”。
别人称“颠覆”,纪德说是“批评”,他承认他的作品“充满肉欲和批评精神”(《纪德谈话录》)。的确,纪德让人不得安生,他无视传统习惯,揭露约定俗成,打乱各种规则,冲破各种限制,挣断一条条锁链。他惹起众怒,群起而攻之。
抨击纪德著作最激烈的人之一,亨利·马西斯就写道:“这些作品里受到置疑的,是我们立身处世的‘人’的概念本身”(《审判》第二卷)
纪德的敌人在抨击他的长篇大论中,却也触及到了他这些作品的核心:人的概念,即在没有 上帝的世界中,人存在的理由。
尼采说:上帝死了。纪德就提出人该怎么办。历来人的问题就是上帝的问题,灵与肉分离。 纪德认为上帝的问题变成了人的问题,灵与肉一体;追求肉欲的快乐并不是罪孽:“您凭哪个上帝,凭什么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他在《人间食粮》中完成的这种解 放,在三十年后发表的《如果种子不死》中又有回响。
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种深厚的天性,没有了上帝,人要做真实的自我,就有了无限可能。人有了无限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要面对层出不穷的个人问题、社会和时代的问题。人争 取解放容易,做个自由人就难了,难就难在生活的多样与变化,要由自己做主进行选择。出人意料的是,纪德选择了难上加难,他选择了生活的多样,跟随生活的变化。
纪德自道:“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相互辩驳。”“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如果种子不死》)
无需选择,内心的复杂与生活的复杂一拍即合。生活犹如他童年所看的万花筒,能变幻出光 怪陆离的奇妙图景。同样,纪德感到他“自身有千百种可能,总不甘心只能实现一种”(《 日记》1892年)显然纪德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应选择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而应时刻 迎候我们内心的任何欲念,抓住生活的任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