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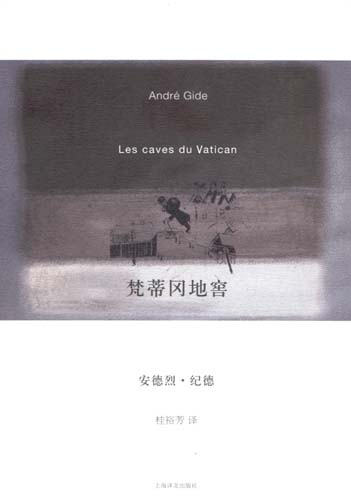 写安德烈·纪德总有种强烈的困惑缠绕着我。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总有人把他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比作法国文学的两座丰碑。但我发现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很容易,只需捧起那几卷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来阅读,一个痴迷于回忆与时间变形的文学大师形象顷刻立显。但对于纪德来说,情形似乎变得复杂起来,我读他的小说越多,反而形象更为模糊。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他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模式,他信奉自由行为,他是法国文学的巨大背景,他的身影深深地藏在《新法兰西杂志》的后面,他混迹于众多法国作家中间,多数时间不动声色,但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 写安德烈·纪德总有种强烈的困惑缠绕着我。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总有人把他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比作法国文学的两座丰碑。但我发现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很容易,只需捧起那几卷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来阅读,一个痴迷于回忆与时间变形的文学大师形象顷刻立显。但对于纪德来说,情形似乎变得复杂起来,我读他的小说越多,反而形象更为模糊。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他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模式,他信奉自由行为,他是法国文学的巨大背景,他的身影深深地藏在《新法兰西杂志》的后面,他混迹于众多法国作家中间,多数时间不动声色,但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特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法国的各种思想,不论是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的思想,还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都要以纪德作参照才能说明它的特点。
写作的神秘需求
1869年,纪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者家庭,这个家庭信奉新教。在富有的资产者的循规蹈矩和清教主义墨守成规的夹击下,作为个体的纪德很早就意识到了内心的压抑,一方面他暗自庆幸财富使他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不会因为受到社会的隔离而痛苦,但与此同时笼罩在童年阴影中的清教氛围则成了他内心深处冲突的根源。
对固有规范的敏感,对律法的遵循,对宗教改革中自由的恐惧,对肉体和性的极端厌恶和蔑视,对罪恶感的自我忏悔无不时刻浸染着他弱小脆敏的心灵。像当时许多的作家一样,年纪轻轻的纪德身体羸弱,很少接触外界,内心的冲突加剧分裂,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单调乏味,自然会隐遁到一个梦幻的世界中。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作家成名之前的某种套路,但对纪德而言,他对外部真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会更强烈,这种感觉甚至驱使他要么以为外部世界不存在,要么就是将外部世界复杂化到一种神秘的程度,以便他在同样神秘的个体世界种寻找自我。
人们曾经描述过着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天纪德对保尔·瓦莱里说:“假如我不写作,我就自杀。”这种写作的信念带来的一个成果是,1891年纪德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这本处女作凝聚了他的文学抱负。他对自己的小说信心满满,认为这本书会满足时代的各种诉求,能够解答大众各种类似的困惑,因此既是“一份长篇宣言”,也是“一份爱情公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并未受到很大关注,卖出了不到二百册。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写作和旅行,截止到1901年,《背德者》的完成,纪德生命中的第一个时期完成了。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写了九本小说,两本评论集,这些创造似乎预示了这个一直都声名不彰的写作者的破茧成熟,而成熟的标志则是1909年的《窄门》。在这本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中,纪德转而向少年时期最隐秘的材料中寻找写作的源泉,甚至不惜公开使用自己的日记,糅合了纪实与虚构,倾注自己的全部激情,书写了一曲凄美的爱情传奇。
然后是1914年,他发表了小说《梵蒂冈地窖》,用他的话说,这是一部“傻剧”,讽刺的手法,传神的描述,曲折的情节,可笑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拉夫卡迪奥,信奉一种自由行为理论,即是说,任何决定都无法解释和理解行为,行为就是行为本身唯一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他甚至无缘无故把一位火车上的旅客推出了车厢。这个人物对战后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影响甚大。从这部作品开始,纪德开始了不一样的写作,一种战斗性质的写作,用一种讽刺喜剧的形式,反抗一切虚伪的宗教,人类和社会。
纪德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法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我们都熟知二战以后是萨特的天下,而在二战以前毫无疑问应该称作是纪德的时代。当然这种成功对纪德来说,有些姗姗来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佳作,但是直到一战后才真正被读者知道。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放纵自己的个性和名声,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了各种媒体的头条和大众饭后的谈资。尤其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每一本书的写法都不一样,时而神秘,时而浮华,他的一个个变化令人有种目不暇接的震惊。但是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卦、爱情、乱伦、性取向、恋童癖。事实上,他始终为压在他性生活上的禁忌而痛苦不堪,很久以来,他就打算写一本描写同性恋的书,甚至打算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觉得说出来不但是为了自我解放,也是为了解放所有被世俗和宗教偏见制造出来虚伪所折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