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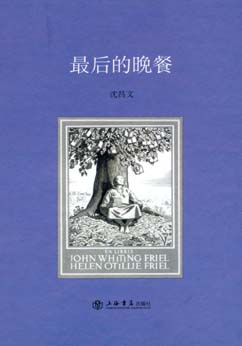 沈昌文,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人称出版界泰斗、文化界元老、思想经纪人,至于他的自称那可就多了:在任时是“小书商”,退休后自贬为“业内临时工”,当然民间流传最广的乃是其自制标签“不良老年”。 沈昌文,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人称出版界泰斗、文化界元老、思想经纪人,至于他的自称那可就多了:在任时是“小书商”,退休后自贬为“业内临时工”,当然民间流传最广的乃是其自制标签“不良老年”。
因了他的两本新书《最后的晚餐》和《书商的旧梦》的出版,记者日前在北京三联书店二层的咖啡厅见到了这位“不良老年”。
老先生递过来的名片很“酷”,用使用过的A4纸裁切而成,空白面上印着一幅漫画,上面的人与他不光形似,而且神似:农民般的脸,板寸平头,卷着裤腿,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包,手里拎着两捆旧书,旁边写着四个字——废纸我买!据说该画出自沈从文的孙女沈帆之手。
“我最近买旧书买得入迷了,有两家旧书店几乎天天去,一家在隆福寺,一家在灯市口,一块钱一本,我经常能发现好书。”说到书,老爷子双眼熠熠生辉。
沈昌文说话很“洋”,随时会蹦出一两个外语单词。而且早已年过古稀的他还有“网瘾”,每天上网时间达五六个小时。“看新闻,看名人博客,偷窥呀。”沈公狡黠一笑,“方舟子跟人吵架我能不看吗?徐静蕾的博客我能不看吗?不看就和别人对不上话了。”
冒充有背景的工部局子弟上了好学校,失学后成了首饰店业绩最好的伙计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用沈昌文的话来说,“父亲是上海大户人家好吃懒做的小开”,一辈子没有做过事,一天到晚只是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昌文和外婆、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
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宁波人是最优秀的,所以沈昌文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昌文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昌文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
十三岁时,沈昌文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很快,他的机灵劲使他在众多来自乡下的伙计中脱颖而出。
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大兵就害怕,而沈昌文不但不害怕,还耍了一个小聪明,他用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往往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业绩最好的伙计。
1947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黄金买卖被禁止。老板的银楼难以为继,只得遣散店员,只留下沈昌文等一两个人。店里一方面从事黑市交易,另一方面与撤退到四明山的一支新四军部队35支队秘密交往,帮忙采购药物、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沈昌文对这些来自苏北的人至今印象深刻:“他们穿的衣服像农民一样,但把破棉袄解下后,却露出了一串串系在身上的金戒指。那是从地主富豪那里没收来的。过了几天,戒指卖掉,要的东西也买到了,这些人就西服笔挺离开了。”
开假证明应聘,跌跌撞撞进三联,“投机”翻译的书改变了命运
1951年,恰逢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他跑去报名。“当然,也做了点手脚。上海人都喜欢玩小聪明的。”沈昌文提起往事时乐不可支,一脸“坏笑”。他说当时人事干部是从延安来的,“不知道上海人会搞假冒伪劣这一套。”于是他通过一个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图章,写上“上海《学习报》社,兹推荐本报记者沈昌文”。其实所谓上海《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
几个月后,沈昌文被从上海派到北京工作。他捡起了自己半吊子的俄语,不但自学还开始试着翻译苏联著作。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走了一条讨巧的路子,翻译了两本书,一本是介绍苏联在编辑出版流程中如何实行定额考核,一本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沈昌文说自己的投机投对了:“懂俄语的人不懂出版的事,搞出版的人不懂俄语,最后居然出版了。”
做校对,沈昌文曾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抗朝”。不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53年的“洗澡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沈昌文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丑恶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包括如何隐瞒“学徒史”造假开证明,包括朋友中有一个是小偷,包括为了挣钱上学曾帮资本家做过假账等等。“当时有一种观点,要把自己说得坏一点,才算忠诚老实。”沈昌文说,结果思想汇报交上去后,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历史太复杂”,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
然而这时,他翻译的那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昌文平步青云,被评为“青年先进分子”,入了党,在党组织的张罗下结了婚,后来还进入候补领导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