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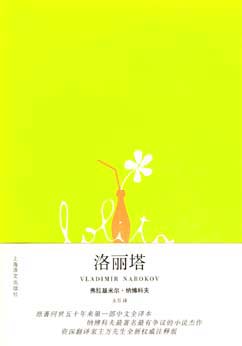 在小说《洛丽塔》里,我们其实看不见洛丽塔本身。作为男主人公亨伯特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以及“罪恶、灵魂”,洛丽塔的形象始终如同一颗洋葱——读者一层层剥下去,偶而激出一层迷惘的泪光来,但剥到最后,你得不到一个确定的可以称之为“内核”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明白,前半部洛丽塔的妖冶“勾引”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或者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亨伯特的主观投射。在小说的第三自然段,亨伯特说:“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必须指出,这个让亨伯特获得初次性体验的小女孩名叫安娜贝尔,典出于爱伦·坡的著名诗作《安娜贝尔·李》——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刻意与现实性划清界限的姿态。纳博科夫将诗里的浪漫意境完全移植到小说中:安娜贝尔因伤寒早夭,也将亨伯特所有的色情幻想,永远地定格在一具十三岁少女的躯体上。经过岁月的消磨,这个原本就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显得越发暧昧难辨,成为亨伯特“闭着眼睛,在眼脸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的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亨伯特说,这就是他后来“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在小说《洛丽塔》里,我们其实看不见洛丽塔本身。作为男主人公亨伯特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以及“罪恶、灵魂”,洛丽塔的形象始终如同一颗洋葱——读者一层层剥下去,偶而激出一层迷惘的泪光来,但剥到最后,你得不到一个确定的可以称之为“内核”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明白,前半部洛丽塔的妖冶“勾引”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或者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亨伯特的主观投射。在小说的第三自然段,亨伯特说:“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必须指出,这个让亨伯特获得初次性体验的小女孩名叫安娜贝尔,典出于爱伦·坡的著名诗作《安娜贝尔·李》——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刻意与现实性划清界限的姿态。纳博科夫将诗里的浪漫意境完全移植到小说中:安娜贝尔因伤寒早夭,也将亨伯特所有的色情幻想,永远地定格在一具十三岁少女的躯体上。经过岁月的消磨,这个原本就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显得越发暧昧难辨,成为亨伯特“闭着眼睛,在眼脸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的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亨伯特说,这就是他后来“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拨开华丽的修辞蛛网,我们找到了关键词“复制”。关于安娜贝尔的记忆诗一般地栖居在亨伯特的意识中,铸就了一副所谓“性感少女”的模板。与其说亨伯特收藏的是一个特定的女人,倒不如说他收藏了一种特定的状态——由他的模板“复制”出的对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长大的。在强韧的想象力的作用下,虚幻的“复制”产生了相当逼真的效果,以至于亨伯特的指尖第一次掠过洛丽塔“细小的汗毛”时,就认定:“洛丽塔已经安安稳稳地唯我而存在了。”
耐人寻味的是,亨伯特之所以成功地介入了洛丽塔的生活,是因为他使用了继父的合法身份。在这位“漂亮爸爸”(法语“继父”的字面含义)开车领着洛丽塔四处流浪的旅途上,他在用洛丽塔宣泄私欲的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暗下决心,“要给这个小孤女一种健全的教育,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纳博科夫不吝篇幅,写亨伯特给洛丽塔置办各色行头的购物清单,写他如何测量少女的身高体重三围乃至颈围大腿围小腿围,写他为洛的13岁生日买了精装本的《小美人鱼》,同时也替自己买了一本《了解你自己的女儿》。与其把他的这些举动理解成天良未泯,毋宁说,潜意识里,他真的将自己代入了“父亲”的角色——那种既对“乱伦禁忌”怀着最深切的恐惧,又在心底深处巴望女儿永远不要长大,从而把每一个出现在女儿身边的男子都当成假想敌的“父亲”。
如是,《洛丽塔》的结局就丝毫不会让人费解了:亨伯特找到当年弃他而去的洛丽塔,口袋里揣着枪却没有伤她半根毫毛,那是因为此时的洛早已长大,远远地偏离了被亨“复制”的性感少女的轨道,报复甚或夺回这样一个褪去了光环的赝品变得毫无意义;而追杀当年诱拐洛丽塔的奎德则变得刻不容缓——在亨伯特看来,正是奎德,强行打乱了他的“复制”工序,最终使得珍宝沦为赝品。亨伯特向着奎德扣动扳机的那一幕,委实威严得像是一名嫉恶如仇的、“真正”的父亲。
回过头来看,亨伯特之前有一段追悔颇具反讽色彩。在他看来,“当初让她去上比尔兹利的那所私立学校,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更明智的办法,是将她彻底隐匿,直到能与其顺利结婚,继而让她生出一个“血管里流着我的血的性感少女”。彼时的亨伯特将通过制度化的婚姻和生育,合法地复制出“洛丽塔第二”,并满怀希冀地开始练习对“洛丽塔第三”做爷爷的技巧……
不过,将洛丽塔送进私立学校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在课间休息时,亨伯特“可以用高倍望远镜从书房里辨别出在洛丽塔四周玩耍的女孩子里有多少性感少女……”凭着这副望远镜,一时间,亨伯特把他的主观世界,变成了一个美丽而感伤的、充斥着复制品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