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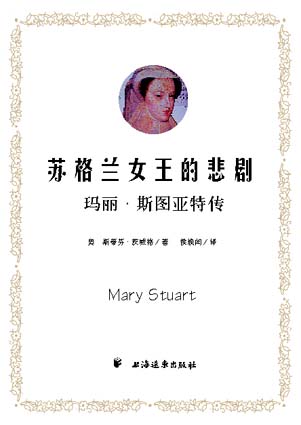 本书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作品之一。通过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叙述,展示了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社会全景。在详实史料的基础上,茨威格既将伊丽莎白与玛丽的矛盾置于上述的大背景中,又不失高明作家的高深技巧,将这种矛盾始终围绕于两个同样掌握权力、但生活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的争斗,使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大大增加。现节选书中最后一章。 本书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作品之一。通过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叙述,展示了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社会全景。在详实史料的基础上,茨威格既将伊丽莎白与玛丽的矛盾置于上述的大背景中,又不失高明作家的高深技巧,将这种矛盾始终围绕于两个同样掌握权力、但生活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的争斗,使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大大增加。现节选书中最后一章。
玛丽·斯图亚特曾为多次喜庆梳妆打扮——为加冕,为施洗,为大婚,为骑士的游艺,为散步,为战争和狩猎,为坐朝,为舞会和比武,到哪里都是服饰华丽,知道美在尘世具有何等的威力。但她在自己的命运最伟大的一刻,为了死亡,她对衣着用尽心思,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她想必在许多天许多星期之前便已考虑好得体的死难仪式,认真地斟酌了每一个细节。一件件衣裳挑来挑去,兴许挑遍了她所有的衣箱,要为这空前未有的场合选一套最最合意的服装。作为一个女人,她很可能在最后一阵卖俏的冲动中,想给后世千秋万代开创一个例子,叫子孙后代看看一个女王应该以一个多么完美的形象去迎接死刑。从六时到八时,花了两个钟头,侍女们侍候她更衣。她不愿意像一个可怜的罪犯,穿着可怜巴巴的破衣烂衫登上断头台。她为最后一次远行选了一套华美的盛装,最端庄最雅致的深褐色丝绒衫,镶一圈貂皮,白色的立领,多褶的衣袖。一件黑缎斗篷裹住高贵华丽的衣裳;沉甸甸的拖地后襟极长,由她的侍从长梅尔维尔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从头到脚,罩一袭寡妇白纱。精工制作的披肩和贵重的念珠代替了世俗的饰物。白色的羊皮鞋着地极轻,后来走向断头台时,死一般的寂静竟没有被她的脚步打破。女王亲手从一只珍藏的箱子里取出一方手帕,后来她的眼睛就是用这方手帕蒙住的。那是一块薄若蝉翼、如烟似云的麻纱,镶着金花边,想必是她本人的作品。她衣服上每一个扣绊的选择都寓有深意,每一个细枝末节都配合着总的音乐效果。她预见到她在断头台前得在陌生男子众目睽睽之下抛开这神秘的辉煌。预见到鲜血淋漓的最后一刻,玛丽·斯图亚特贴身穿了一件大红绸衬裙,还吩咐下人给她准备一副长过胳膊肘的火红色手套,以便斧子迸起的鲜血溅到她的衣裳上不太刺目。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死囚赴死时如此精心构思过自己的死亡,如此意识到自己的不凡。
上午八时,来使敲门。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应声。她正跪在读经台前念临终经文。念完才站起来。第二次敲门她才去开。门开处,进来的是郡长,手持白色的权杖(马上就得把它折断),深深地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说:“夫人,勋爵大人派我来请,他们等着您。”“走吧。”玛丽·斯图亚特说,向门口走去。
最后一次出行开始了。左右都有仆役扶持,艰难地挪动患有关节炎的双腿。她为了抵御一阵阵突然发作的恐惧,动用了三种宗教手段来保护自己:颈挂一具金质十字架,腰垂一串宝石念珠,手持善男信女的宝剑——一具象牙的耶稣受难像:让世人瞧瞧,女王至死心怀天主教,以身殉教。世人会忘记她的青春有多少罪孽和疯狂,忘记她是作为蓄意杀人的同谋犯登上断头台的。她希望千秋万代都以为她是为了天主教事业而受苦受难的,是身受异端敌人之害的牺牲品。
她的忠心耿耿的臣仆送她搀扶她到门口为止——原来就是这样设计这样决定的。因为不能让人觉得他们参与了可耻的杀害,以为他们主动把自己的女主人送往刑场。他们只愿意在她的居处侍奉她,但不愿在她惨死的时刻做刽子手的帮凶。从门口到梯子跟前,由埃米亚斯·波立特的两名部下陪同。只有她最凶恶的对头才做得出这样的事——在弥天大罪中充当帮凶,把加过冕的女王押往断头台。断头台脚下,行刑的大厅门口,她的侍从长安德鲁·梅尔维尔跪在梯子最底下一级前等她。他作为苏格兰贵族,有责任把死刑经过奏报詹姆斯六世。女王扶起他,拥抱了他。这位可以信赖的见证人到场,使她大为宽心,增加了她起誓要保持的内心的宁静。梅尔维尔说:“我负起我一生中最沉痛的责任——把我至尊的女主人的去世报告给国内。”她回答:“恰恰相反,你应该为我的考验即将结束而高兴。只是要你报告:我至死忠于我的宗教,始终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苏格兰的真正的女儿,历代国王的真正的子孙。让天主原谅那些盼我死的人吧。还请你告诉我的儿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可能伤害他的事情,从来没有损害过我们的统治权。”
说罢,她转身向施鲁斯贝里伯爵和肯特伯爵请求准许她的贴身女侍在场观刑。肯特伯爵反对。他说,这些女人的号叫和哭泣会把刑场搅乱,引起不满,因为她们准要拿她们的手帕沾女王的鲜血。玛丽·斯图亚特坚持她最后的愿望。她说:“我保证她们绝不会这样。我想不出你们的女主人会拒绝一个身份同她相等的人的请求,不让她的侍女侍候她到最后一刻。我不信她会给你们这样无情的命令。即使我没有这样崇高的位分,她也会答应我的请求,何况我还是她的近亲,是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是法国的前王后,加冕御极的苏格兰女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