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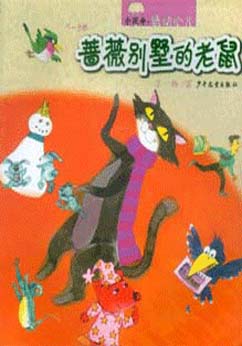 1999年夏天,王一梅创作了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标志着她的童话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把她和那只默默无闻而又充满幻想、并能创造奇迹的小蚂蚁联系起来,我总觉得她就是那只在书本里的小蚂蚁。2003年春天,我在她刚出版的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的封面上读到她的一段十分醒目的题词: 1999年夏天,王一梅创作了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标志着她的童话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把她和那只默默无闻而又充满幻想、并能创造奇迹的小蚂蚁联系起来,我总觉得她就是那只在书本里的小蚂蚁。2003年春天,我在她刚出版的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的封面上读到她的一段十分醒目的题词:
有一只默默无闻的小蚂蚁,在书本里慢慢的爬行,幻想着春天的花朵。有一天,蚂蚁忽然发现,它爬过的书本已经变成了美丽的宫殿。
这就是说,王一梅也是把自己当作那只书本里的小蚂蚁的。这是王一梅自己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很值得重视。
一个作家总会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感情和愿望,用艺术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来。王一梅也不例外,她在《书本里的蚂蚁》中似乎想表达这样一个自我评价:平凡的小人物--美丽的理想--不懈的努力--把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一个真率的艺术宣言,蕴蓄着一种既谦逊又自信的情感力量和人格魅力。
从那时开始,我读王一梅的每一篇童话,仿佛觉得都有一只快乐的小蚂蚁在那上面兴致勃勃地穿行。
《鼹鼠的月亮河》中那只叫米加的黑色小鼹鼠,不就是一只小蚂蚁吗?他不像他的哥哥们有棕色发亮的毛,他又瘦又黑,与众不同;他爱幻想,爱思考,爱发明创造;敢于闯荡世界,经受各种磨难而不气馁;他终于有所作为。
《雨街的猫》中那只遭人遗弃、饱经风霜的流浪黑猫阿洛,不也就是一只小蚂蚁吗?他出生在贫穷的风街,遭人遗弃后到处流浪。阳光街本应是爱晒太阳的猫最好的栖身之所,却没有他的落脚之地。他只能住在流浪人汇集的雨街,因为这里有善良的雷莎太太会收养他;也只有在这里他的音乐天赋才得以发挥,在几经曲折之后终于成为出色的小提琴家。
《第十二只枯叶蝶》中的那第十二只枯叶蝶,也是一只小蚂蚁。一只天生丽质的蝴蝶,却是枯叶般的外表,这就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只能与枯叶为伍。然而,它以自己的善心,给孤独的乌鸦带去温暖,而它的美丽也终于为乌鸦所发现。
……
总之,在我的眼里,无论是书本里的小蚂蚁还是第十二只枯叶蝶,无论是月亮河的小鼹鼠米加还是住在雨街的流浪猫阿洛,它们都是一种既谦逊而又自信的品格的象征, 都寄托着王一梅所要表达的普通人的审美理想和善良而真诚的情感愿望。
是的,王一梅是用自己的普通人的审美立场和真诚的思想感情来创作童话的,并且在作品中努力张扬一个具有她的个性特征的情感主题──从平凡中崛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理想。我认为,这是王一梅童话之所以让人感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我想到了安徒生。安徒生不也是“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的”吗?王一梅也许正是从这位前辈童话大师那儿领悟到了童话创作的真谛,从而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作她所描写的重要方面。
这样,就出现了童话的自我象征。
我们自然不会忘记被人们称作安徒生的自传式童话的《丑小鸭》。那是安徒生“自我象征”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认为,恰恰是安徒生的《丑小鸭》对王一梅的童话创作产生了影响。对王一梅来说,这种影响有主动接受(或者说有意识的接受)的,也有被动接受(或者说无意识的接受)的。
从主动接受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先看看《鼹鼠的月亮河》中的一个细节──当鼹鼠米先生一家看电视看到动画片《丑小鸭》时,鼹鼠老大提出了一个问题:“妈妈,米加(就是那只与众不同的黑色鼹鼠)是我们这里的丑小鸭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论鼹鼠妈妈还是其它鼹鼠兄弟几乎是异口同声的:米加就是丑小鸭!王一梅运用这个细节,显然是要写出米加的与众不同,写出弥漫着传统观念的周围环境(包括鼹鼠妈妈和鼹鼠兄弟等)对他的不理解;换句话说,王一梅显然是想把鼹鼠米加塑造成丑小鸭式的童话人物。
于是,在我的眼前,月亮河的小鼹鼠米加呀,书本里的小蚂蚁呀,愿与寂寞的乌鸦作伴的第十二只枯叶蝶呀,住在雨街的黑猫阿洛呀,仿佛又都变成了丑小鸭式的童话人物。我想,我这样推论,应该不是牵强附会的。只要你细细地加以比较,王一梅笔下的这些童话形象和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形象是属于同一情感类型的。
从被动接受的角度来说,“丑小鸭”这个童话形象,由于其自身的典型性和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深入世界范围的广大人群的心灵深处。即便是在与丹麦远隔千万里的中国,我们在普通人群中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自我表述或自我评价:“我是一只丑小鸭!”王一梅,这位从少女时代便从寻常百姓家庭走出来、并且曾经长期生活在幼儿园这样平凡的教育岗位上的普通幼教工作者,恐怕也不能例外,这种“丑小鸭”情结也许早已在童年时代便已进入她的无意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