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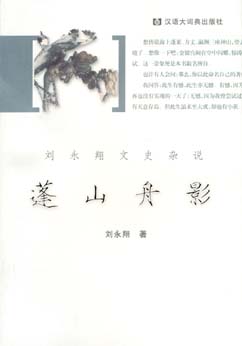 刘永翔这个人很低调,有才有学却绝不张扬,读书界以外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文史学者中佩服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要从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说起。 刘永翔这个人很低调,有才有学却绝不张扬,读书界以外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文史学者中佩服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要从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说起。
1982年第一期的《文史知识》杂志上,刘永翔写了一篇不长的读书札记《“折柳”新解》,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致酒行》中的一个词作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想不到竟引起了钱钟书先生的注意,并在第二年给《文史知识》编者的信中加以赞扬,这当然使时年三十五岁的刘永翔心潮澎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向自己的崇拜者倾吐怀抱的愿望,许多文人皆有“万言书”之作,但刘永翔却选择了更艰难也更见其才力的文体——骈文,他在1983年4月16日所写的《上钱钟书先生书》,我已读过好几遍,但每读一遍都禁不住击节赏叹。如这一段陈述自己命运的:“翔於越下材,春申寄客。命常多舛,生实不辰。岁在丁酉,时甫十龄。朝廷生弭谤之心,寰海起川防之役。家严乐在育才,方勤于周序;直能忤物,难免于罗钳。名登党人之碑,家堕民之籍。始则谪迁于陇亩,后则编管于闾阎。然狱虽沉三字之冤,节未改孤忠之介。梦尚萦乎白鹿,望犹寄于金鸡。讵意苍狗云成,红羊劫起。身竟箝于楚市,命仅脱于秦坑!呜呼,毕郑玄辰巳之年,死犹可羡;入柴望丙丁之鉴,生祗堪伤!……所幸九有难沉,四凶终殛。汤网开而党锢解,楚囚释以冤狱平。家严黉宇重回,教筵复掌。翔则不犹可炼,桐未全焦。戊午岁,以同等学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为研究生。从此置身庄岳之间,学步邯郸之市。两年毕业留所。学惭半豹,命作校书;才谢八叉,除为助教。人笑溺虫鱼之学,自欣识鸟兽之名。……”这些句子一联一联地喷吐而出,严密的规律和工整的典故,都挡不住他久已郁结于心中的一腔热血与才情。他的文字越是典雅,他的情感越是激越,我们汉民族语言文字在他心火的冶炼之下,竟能熔铸出如此美妙的文辞。这里不只是学问才华,更使人感动的是一位年轻学人的跃动着的心。我以为可与古代才人的杰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媲美。
这使我想到骈文这种文体究竟还有没有生命力了?它的属对要工,文辞要雅,精镂细刻,剔透玲珑,当然不可能是“大众化”的作品,但对于能够欣赏其价值的人来说,它自有不可替代的艺术光芒。这正如红氍毹上的昆曲、寿山石上的雕刻、景德镇烧的细瓷乃至鼻烟壶里绘制的内画……是一宗文化遗产,是国粹,它总得有人懂,有人会,有人欣赏,有人保存。
刘永翔的这封信,当然赢得了钱钟书先生的褒奖,因为钱先生对骈文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管锥编》中论徐陵的《与杨遵彦书》时对骈文的价值说了一大串精到的意见。在给别人的信中也说:骈文“少而好之,熟处迄今未忘。”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忽奉损书,发函惊叹:樊南四六,不图复睹。属对之工,隶事之切,耆宿犹当敛手,何况君之侪辈!”刘永翔的确是长期在历史文学的典籍中漫游,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资源,才形成了他惯于把自己的才思用对偶骈俪的形式表述出来。他在《自题诗集》中自述:“领略江山匪所长,每凭故纸助文章。爱将换骨新诗句,贮入通眉古锦囊。但使腹中书戢戢,何劳潭底影徨徨。平生不解骑驴出,谁道辞无日月光?”——这话也不错,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自己惯于使用的武器,只要有真性情真才思,自有其不可掩盖的光彩。
在这本集子里还有许多谈文说艺的文章,长的如《谈名说姓》,短的如《〈推背图〉与〈烧饼歌〉》,考证的如《〈陋室铭〉作者之我见》、《周邦彦的家世》,还有类似《世说新语》的《钱通》……都大有可读之处。
刘永翔是刘衍文先生的长子,刘老先生有“誉儿癖”(“誉儿癖”原是王安石的故事)。当刘老先生看到钱钟书的赞誉之后,也情不自禁地吟诗道:“誉儿莫笑王家癖,曾入梁溪巨眼来!”(钱钟书无锡人,无锡古称梁溪。)老先生的心情我是能体会的,我们毕竟也都是有儿女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