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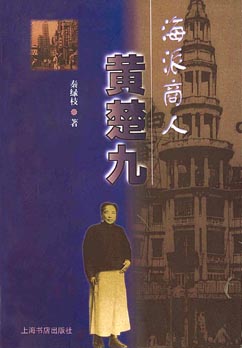 十五、一记耳光· 新新舞台能邀请到这位“伶界大王”,自是如同迎接钦差一般,丝毫不敢怠慢。后台经理周咏棠特地派了王荣祥(艺名筱荣祥)专程到北京,陪同老谭及全班人马乘轮南下。船到码头,已有汽车在等候,这是黄老板的车子,今天自己不用,空出来给谭老板乘坐。 十五、一记耳光· 新新舞台能邀请到这位“伶界大王”,自是如同迎接钦差一般,丝毫不敢怠慢。后台经理周咏棠特地派了王荣祥(艺名筱荣祥)专程到北京,陪同老谭及全班人马乘轮南下。船到码头,已有汽车在等候,这是黄老板的车子,今天自己不用,空出来给谭老板乘坐。
已经为谭老板租了房子,就在小花园西首对面的宝和里内,这里离戏馆很近,谭老板尽可在家里过足了瘾,养足了精神之后再去后台扮戏,来得急
谭老板的包银讲明是一万大洋,其他重要的配角是每人六千大洋,都管吃管住,管接管送。打鼓的是刘顺,操琴的是裘桂仙,即裘盛戎的父亲。裘桂仙改唱花脸后,人们说他的行腔有老生韵味,这可能与他曾为老谭操琴,受其熏陶有关。
老谭的一些拿手戏,如《空城计》、《琼林宴》、《洪羊洞》等,都演了四次;《托兆碰碑》、《乌盆计》演过两次,其他只演过一次。尤以与金秀山搭配的戏,如《空诚计》、《捉放曹》、《黄金台》等,旗鼓相当,最为精彩。老谭还演过一次《坐楼杀惜》,配演阎惜姣的是上海的名旦一盏灯(张云青),他以前曾和老谭合作过,彼此熟悉对方的戏路,所以也演得丝丝入扣,非常默契。
这次老谭还演了以前到上海没有演过的《连营寨》(即三国中的彝陵之战),剧中有大段“反西皮二六”的唱段和火烧时的跌扑身段,让上海观众有一新耳目之感。相传老谭在清廷供奉时,一直不唱此戏。但戊戌政变后,每逢光绪皇帝生日,西太后却要老谭唱《连营寨》。当演到刘备“哭灵牌”时,台上站的大小将官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不哭就得不到赏赐。西太后的用意,是当着光绪的面,纪念她死去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
《胭脂宝褶》(又名《失印救火》)也是老谭以前没有在上海演过的,这次也演了。这是一出做工戏,老谭在剧中演白槐,有繁重的道白和做表,把一个老于世故的公门中人刻画得维妙维肖。后来马连良演此戏,又加以丰富和提炼,成了马派的代表作。
《长亭昭关》和《朱砂志》,人们向来认为是汪桂芬和孙菊仙的看家戏。这次看了老谭演出,才发现他自有特殊的风格,从此谭迷们纷纷风从,不唱这两出戏则已,一唱就以“谭派”为标榜。但他们多半是跟张翰臣、陈彦衡这两位谭派行家学的。
“伶界大王”这次在上海的风头比以前更健,口碑好得更是不用说,上海的好些尚未成名的同行常常抽空到新新舞台来看老谭的戏,偷学他的“玩意儿”。但一些已经出了名的“角儿”则对“大王”之称不服气,等机会想要老谭的“好看”。
一出《盗魂铃》成了爆发点。
《盗魂铃》是出玩笑戏。讲猪八戒奉了师父之命,到妖怪那里去盗魂铃。谁知他贪玩心切,偷空溜到一个地方睡足懒觉之后,又戏瘾大发,把他会唱的各种戏曲都唱了一遍,这其实也是让演员显本事给观众看,并制造一种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热烈气氛。
上海有个杨四立唱《盗魂铃》很有名。杨四立的本行是武丑,但也能唱老旦和老生戏。他演《盗魂铃》,除了卖弄他会唱时新曲调外,还能从四张桌子的高处凌空翻落在地,观众每每看到此处,都会狂热地叫起好来。
杨四立时在新舞台,就常贴《盗魂铃》与老谭对抗。
黄楚九一看这情形,便把周咏棠找来商量:如谭老板肯演一次《盗魂铃》,在上海戏迷中造成的哄动,是杨四立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周咏棠奉命来找谭鑫培,委婉曲折地转达了黄老板的意思。老谭一听,沉吟半晌,说:“演是可以演,不过我有我的演法,你们不要拿我当杨四立。”
周咏棠大喜,连说“那是自然”。但杨四立能翻四只台子,谭老板能不能翻呢?上海观众看惯了杨四立,在这一点上恐怕很计较。
老谭又默然片刻,说:“上海人懂戏吗?懂的话,你们也给我放几张桌子在台上,三张、四张,随便!”
周咏棠没有深究老谭说话的意思,只把“随你们在台上放几张桌子”这一句听了进去,回来禀告黄楚九,自然高兴非常,立即贴出海报,刊出广告:某月某日晚,伶界大王准演《盗魂铃》,还特别注一句,“南腔北调,百戏杂陈,翻三张桌子。”
杨四立翻四张,谭鑫培翻三张,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也很不错了。
传说孙菊仙这时也在上海,看了海报,便到庆和里来找老谭,说:“你的武功底子是好,但也不能不要老命啊!”
谭鑫培是武生出身,唱过《金钱豹》,演孙悟空,能在桌上翻锞子下来。但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
老谭笑嘻嘻地说了一句:“山人自有道理。”
到演出的那一晚,外行、内行,都争相来看,新新舞台卖了个满堂。
老谭的学唱,多半是北方戏曲,有皮黄,有梆子,有大鼓等。观众虽然觉得他唱得很好听,却听不出什么究竟来。老谭其实把当时京剧界的一些前辈如余三胜、张二奎、卢台子,还有青衣胡喜禄的唱腔,都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们的神韵,可是台下的观众对这些前辈都不熟悉,所以反映也不怎么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