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毛主席誉为“国宝”的陈垣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和教育家。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著作集”最新两种之一,也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这是陈垣先生在1964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下文为陈垣先生文孙陈智超为该书新版所撰写的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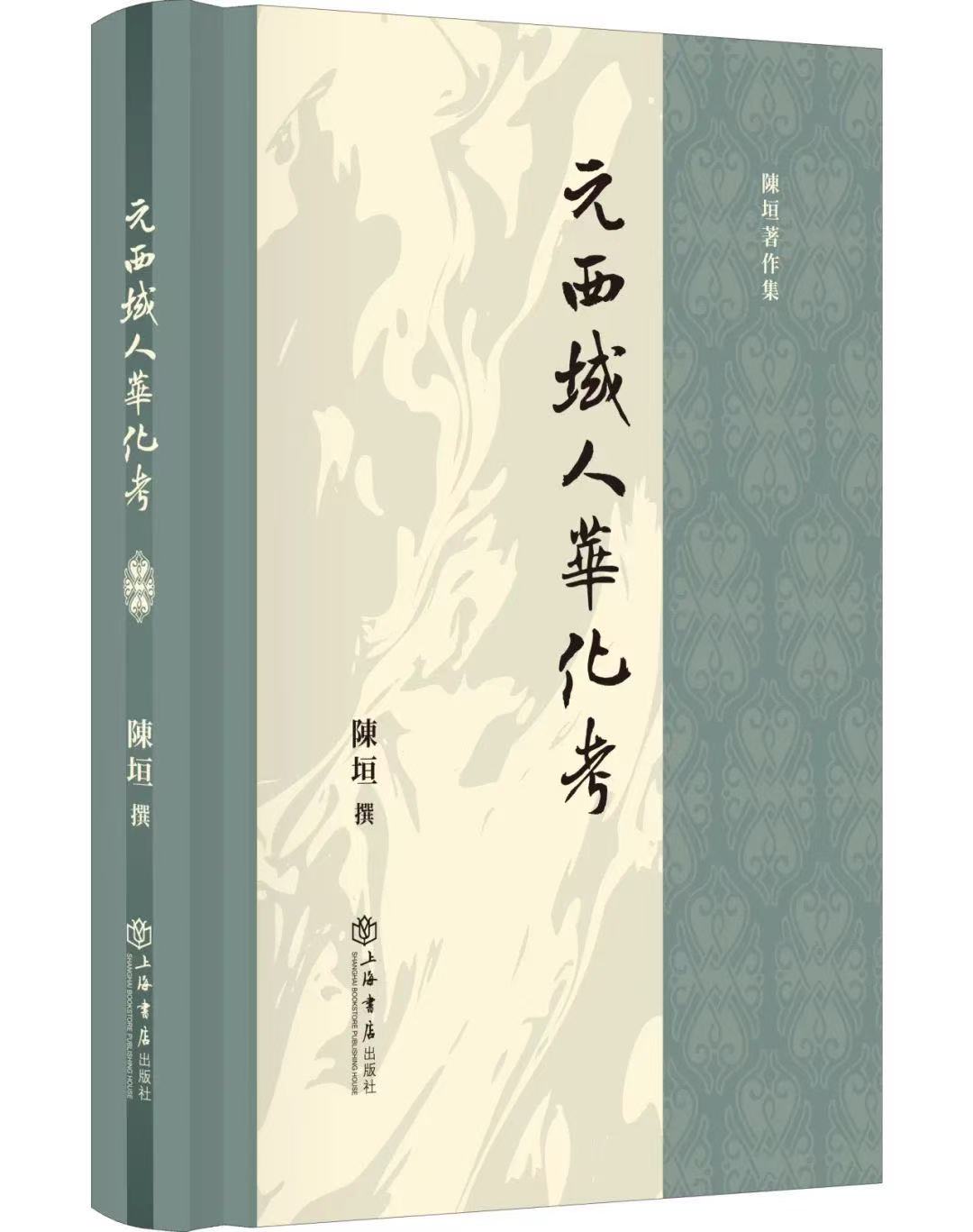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著作集)
陈垣 撰
上海书店出版社
《元西域人华化考》(下文简称《华化考》)作于1923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列强侵略,政客争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二十五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用文字作革命宣传,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残酷的政治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1923年开始,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与教学,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国民体质,处处落后,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就是学术、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为人轻视。据他的朋友、学生们回忆,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
例如,胡适1959年1月3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20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1]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 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
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1978年回忆道:“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3]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4]。
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5]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写作,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代,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絶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华化考》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年至一三六○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在书中郑重声明:“吾之为是编,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卷二第五节)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西域”及“华化”两词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