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文遗录》是从宋人文集、宋代史籍、宋元明方志、宋人法书、宋代墓志碑刻,以及新发现和新出土的文献中,辑录《全宋文》未收集或已收但有较大差异之宋人文章,共计近三千篇,加以考订、校勘、排序、标点,撰写作者小传,按时代、作者和文体编排,分为一百四十一卷,近三百万字,是对《全宋文》的重要补充。下文为本书编者李伟国先生所撰,讲述了编纂《宋文遗录》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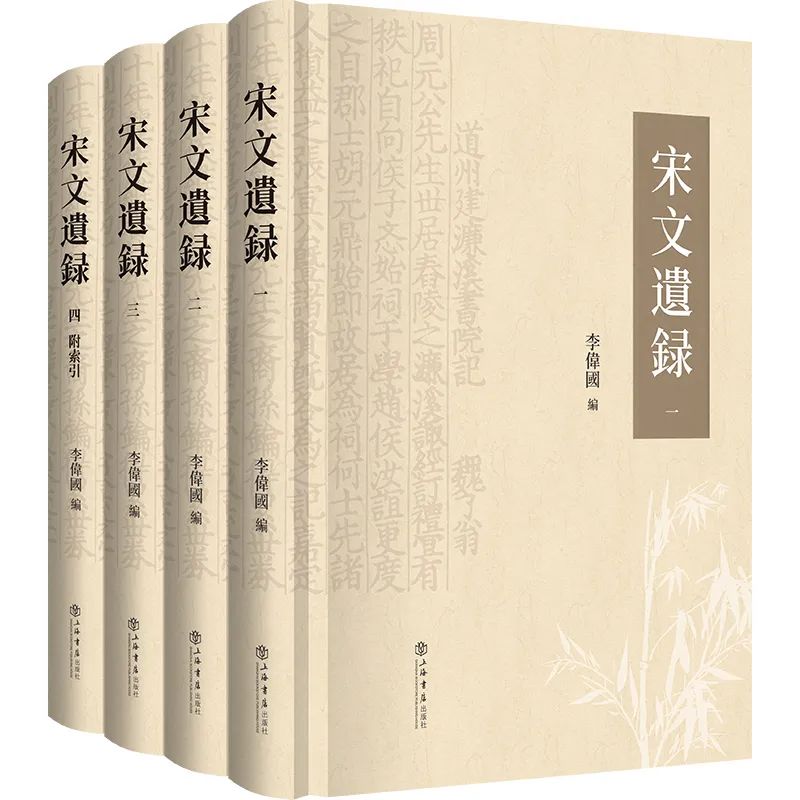
《宋文遗录(全四册)》
李伟国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全宋文》的编纂,与川大古籍研究所的曾枣庄教授、刘琳教授、舒大刚教授,以及各位同仁,都保持着良好的师友关系,关注着他们的学术活动。
2002年,承蒙老友方健先生告知,编纂多年的《全宋文》遇到了出版方面的困难,当时我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在与主编曾枣庄教授多次通话以后,经过社内讨论和评估,毅然只身赴成都与曾、刘等先生商谈,同年请曾先生和刘琳先生等来沪签订了出版合同。
2004年,我离开上海辞书出版社,其时《全宋文》书稿的编辑校对工作尚未完成,我的后任张晓敏社长继续予以推进,并联合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以颇为大气的格局推出全书。在《全宋文》出版之际,2006年8月16日,我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有幸发言并留下了这样几句话:“群贤埋首成都府,穷搜精理廿载苦。有宋一代文章在,书墙巍巍人争睹。”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安徽方面共同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座谈会,集团陈昕社长特意嘱咐辞书社一定要让我参加。此后,《全宋文》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清代以来,搜集一代诗文,标以“全”字的大书的编纂代不乏人。当代盛世修典,唐圭章先生开风气之先,编《全宋词》,录1330余家,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后来则又有《全宋诗》《全元文》等问世。《全宋文》,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宋代文学创作的文章总汇,也是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资料的宝库,包含整个宋朝320年间9179位作者的172456篇文章,编为8345卷,总字数达到1.1亿。在《全宋文》的编纂过程中,除了搜访存世宋人文集以外,还曾普查了浩如烟海的经、史、子各类古籍和金石、方志、谱录等资料,获取了一大批前此不易见到的集外佚文。
此类大书,穷搜旁采,精心校订,囊括一代或数代作家之诗、词、文,标准分明,次序井然,用功极深,功能亦巨。若欲研究一代、数代乃至通代之文学,可从中看到全貌、趋势,亦可研究流派,研究作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一代文体之嬗变等等。其阅读使用之方式则有浏览、通读、细读、反复研读。
更有一项大功用,即所谓“无顺序阅读”。如《全宋文》这样的一代文章总集,同时也是一份大型文献库。作为一座库藏,里面所有的藏品,固然需要安放得井井有条,否则没法登录和取用。但有许多取用其库藏者,他们只需要了解此库藏的大体性质,以便知道其中的藏品是否会有他所需要的东西,至于里面的东西具体是如何安放的,他不了解也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取得需要的东西就好,并且越快越好。
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功能,《全宋文》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宋代文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出版后获得首届出版政府奖。
由于《全宋文》其书编成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除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遗漏,如南宋参知政事葛洪的《蟠室老人文集》,由于未能与藏家谈妥条件而未收入,除未收作者不明的文章等以外,更未及利用编成后新出现的大量图书、数字出版物和出土文献。
而海内外学术界在广泛使用《全宋文》的同时,在各种学术刊物和学术专著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但此类文章虽多,大多为偶然发现或一得之功,就“增补”本身来说,只是提供了诸多线索,总量毕竟有限。历代诗文总集的编纂,既是意义重大、价值极高的课题,也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课题,在一书出版以后,陆续进行补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仍有巨大的空间。
在我离开出版工作的职业岗位以后,即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宋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贡献绵薄之力,并开始多方访求《全宋文》尚未收录的宋人遗文。2011年,在集团领导的支持下,我设计了《全宋文专题数据库》项目,得到上海市经信委资助,在完成《全宋文》数字化的同时,补入了30万字的佚文。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小有所成,积累了二三百万字,成《宋文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