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经常出现,我们写的研究计划其实是为了在田野中修正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太相信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把别人的经验打造起来。社会学并不是这样,社会学有些时候也会修正,但是相对而言还是会强调这个框架本身的稳定性,你不能随便动摇这个框架。所以人类学的体验当中会发现一个问题,学者本来是沿着传统的问题意识去的,结果发现别人生活当中的逻辑是大于你研究的逻辑的,我们的任务等于说,你必须要顺着别人的逻辑走。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东西就一定先进,但是它有一种很明显的学科意识。
人类学我经常讲一点,就是人类学家其实很奇怪,我们一方面非常强调书写的重要性,比如民族志的写作,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很不相信语言,所以总在找在语言可表述和不可表述之间的那些东西,至少现在表征的强调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说,我告诉你这些符号,这是一套系统文本什么的。很多人会强调,你看我今天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怎么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买东西,这种碎片式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对话,也会发生被观察者自己的解释,但是实际问题是,我作为研究者是要去想,在他的生活内部,整个从表述到决策到行动的过程为什么能成立,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对方未曾觉察的一部分。
很多人说你们人类学写作越来越像文学,但是你们的解释越来越像哲学,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对那种非常成体系的,认为自己能够给社会建立一个框架,然后把某些问题支撑起来的理解方式是保持怀疑的。
最初的人类学,本来是寻找特例
袁长庚:人类学在发展历史上,本来是去找特例,它本来是告诉西方人,我们西方人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是因为可能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只是我们今天处于工业时期。所以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定位是去寻找那只黑天鹅。
其实人类学早期知识上的启蒙,跟所谓博物学或者早期的探险家是一样的,它们其实都是在收集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奇闻异事,只是它服务的大的目的是想要明确,人类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它们就像今天的化石研究一样,找到一个个时期的某种生物,然后填在进化序列当中的某个环节里。
人类学早期就是这样,也是希望去搞清楚这些人现在停留在什么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理他们。但是大概发展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开始不安分,他意识到西方人的很多的问题意识其实是错的,比如我们都觉得,一个成熟的文明一定是有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的,但是二战前后,这些欧洲人在非洲研究时发现,那个部落其实很大,有几千甚至几万人,但是它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整整整齐的国家机器,它就可以通过分散或结合的方式有一套自己的节奏,而且运作得非常良好。
所以,其实人类学是在二战后通过找这种特殊性的方式去回应西方人自己的。但是这个东西到今天又会转变角色。今天很多人是希望看到特殊性,因为这些特殊性就给所谓本质主义留下空间。我跟你不一样,我们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不要跟我谈你跟我是一样的,也不要谈跟我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别人经常就会说,你今天之所以会觉得你跟他不一样,是因为你忘掉一些常识。
所以我们回到存在的层面,回到日常生活层面,你就看出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经验背后貌似都有一套整齐的逻辑,而且互相之间是有理解的可能性的,这就使得今天的人类学角色有一点改变,就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呈现特殊性的原因和脉络,但是已经不再强调特殊性是人类必然的宿命,我们反倒会在对差异的强调中意识到,可能我们共性的那一面是很明显的,甚至有一个更重要的知识计划是,人类学其实事实上一直是启蒙以来的知识的反叛者,它大概从最初开始就不太相信启蒙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比如大家意识到,最近这几年对于生态危机这种事情讨论得比较多,人类学参与其中就会发现,我们如果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可能要回到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是这样,你认为它天经地义,但是可能不是这样。人类没有天经地义,这些东西是现代性造就的,可能非常短暂,也就100多年200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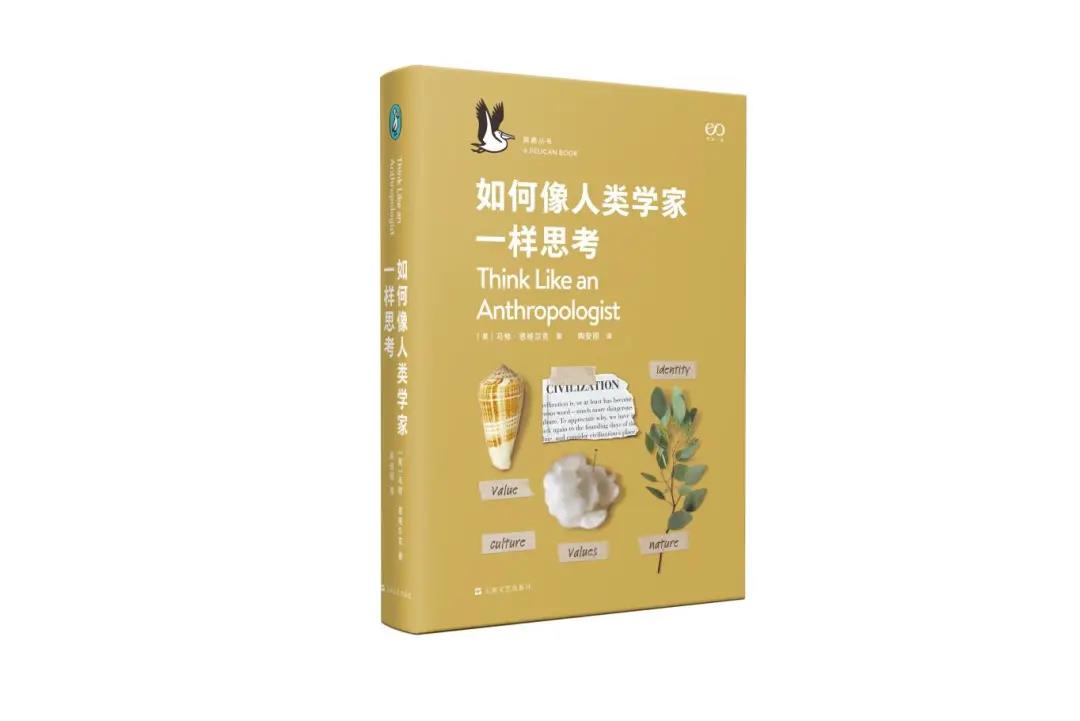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 著
陶安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