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华平教授,辛勤耕耘十余年专门治学的最新成果,也是首部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著。通过编年史这一史著体裁,以明清540余年重大历史的变迁为经线,以明清文人生平、戏剧创作、作品考订、版本流变、历代批评家评论、戏曲传播与演出等为纬线,系统完整地展现明清传奇、杂剧真实、客观的历史风貌,是今人研究和了解古代戏曲的两座高峰——传奇与杂剧的经典之作。本文节选自该书绪论,作者探讨了如何运用编年体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以及戏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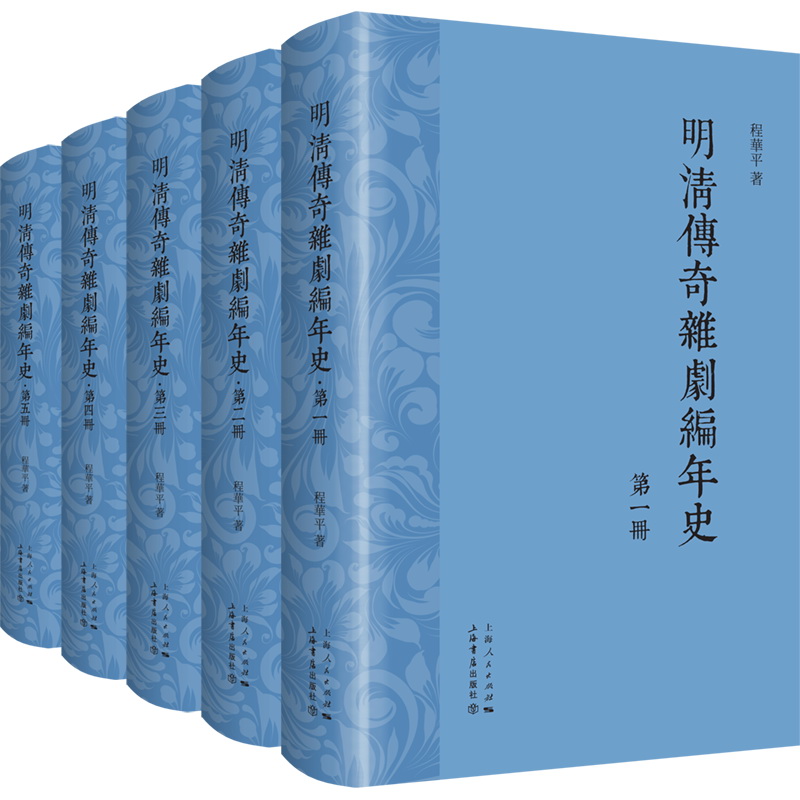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精装本)
程华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开本:16开
定价:680元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1919年,胡适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这样写道:“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拢统研究一番,依年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1]这是胡适认为的撰写史著应具有的态度、步骤与方法,应该说所言甚是。稍微调整一下用词,也基本上适用戏曲编年史的研究与撰写,因为面对历史长河中数百年积攒下来的玉石杂糅、良莠错陈的史料,对任何一位戏曲史家来说,都需要经历“述学、明变、求因、评判”的过程,都需要将这些材料变成史著建构中的“砖瓦”。胡适在这里强调了“完全中立的眼光”,大概是有感于史著撰写中普遍存在且无法避免的撰述者本人立场的“干扰”。……
应该说,完全秉持“中立的眼光”、全部捐弃“陈见”,在史著的实际撰写中是无法做到的。受到撰写者知识背景、学术兴趣、文化身份、政治立场、个性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史家对史料选择的动机无论怎样“纯洁”,终不免有主观情感缠绕笔端。史家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用确凿的史实来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编年体的方式来撰写历史无疑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
首先,撰述的客观性。清末以来,域外史著的章节体撰写方式被国人引进并得以广泛运用,遂成为近现代以来史著结撰最重要的体裁形式。章节体史著具有长于分析、便于综合、体系严整、逻辑性强等诸多优势,然亦常因其部类章节的格局设置,而人为地将作家与作品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有损于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整体性。与此同时,章节体史著通常强着意于对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探寻与总结,用“规律”来观照、统领“史实”,无视某些不合撰写者预想的史料、剔除与之龃龉者,这就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史实的客观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容易陷入“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窘境,甚而“滥用者论人议事,总有摆脱时空束缚的冲动,不愿忍受任何羁绊,以便思想任意驰骋,以致脱离材料与事实固有的内在联系,依主观取舍剪裁,拼凑论据,编造论点,看似自圆其说,实则随心所欲,穿凿附会者不在少数。”[2]其负面影响与后果为有识之士所诟病。
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我国古代历史编纂的主要方式。编年史是建立在对史实客观记录基础之上的,遵循自古以来的修史传统,严谨、细致地对待相关的史料记载,始终做到史有所出,论有所据。当然,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而言的。对史料的取舍、阐释及评价,实际上也受到编写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自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就史料本身来讲,过去的历史事实能否被后人发现与利用,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带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史实本真面貌的追索,对史料的运用、阐释与评价,不趋时,不溢美,不掩饰,不曲解,不因撰写者的好恶而作取舍,而是客观、理性地对待所有史料,尊重史料本身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来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施凤来中廷试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升礼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明史》称其“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3],将其视为“阉党”成员。但在《乾隆平湖县志》中,他却以另一幅面孔被记载下来:“凤来入政府时,珰势张甚,一以镇静调护为务。中使李明道欲催民船转运,奏寝其议;修撰文震孟疏语激怒,将逮治。凤来从容廷辩,自述缇骑逮周顺昌激变一事,感动熹宗,复密揭申救以免;皇极殿工成,魏忠贤叙功爵赏,凤来引祖制非军功不可,而旨从中降,乃力辞恩荫不受,亦不附于珰也。”[4]面对施凤来的“两幅面孔”,戏曲编年史在引用相关史料时,就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加以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