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今年的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回顾这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民族复兴路上,在她的领导下,举国上下赢得了新冠疫情的阶段性胜利。期间中华民族从个人到集体都体现了处危不惊,逆势奋进、万众一心的精神。这种不凡的气质,其根源可在庞朴先生的这篇《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找到相关答案,同样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需要这种精神。以此文与广大读者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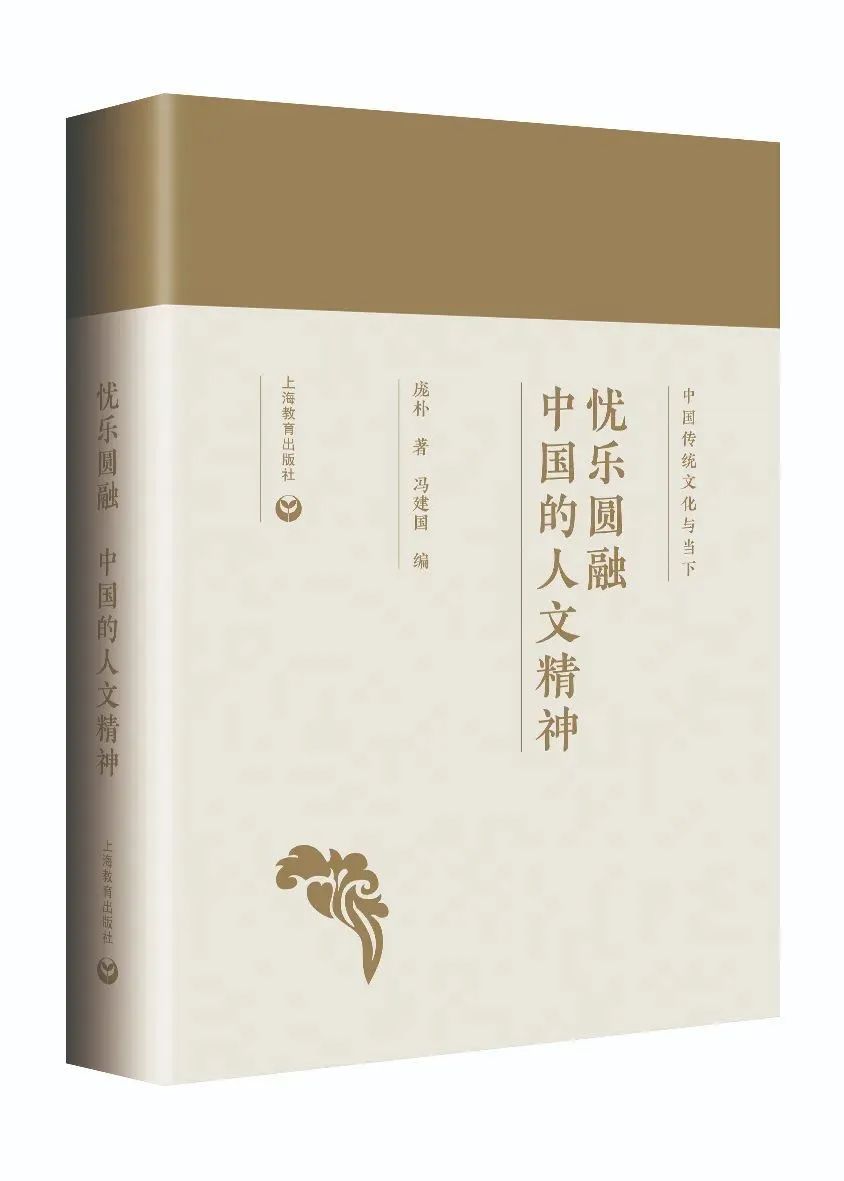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系列丛书)
庞朴 著 冯建国 编
责任编辑:储德天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6月
定价:68.00元
对中华文化特质的界定上,有无数观点。徐复观先生的“忧患意识”与李泽厚先生的“乐感文化”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圈子里,都发生了强烈影响。
分析这一对都已颇具影响的学说对于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课题,岂不也算在尽一点绵力么?!
徐复观提出忧患意识:
人具备自我主体性后的自我把握和升进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过分渺小,一凭外在的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或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取词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 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
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 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 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
李泽厚提出“乐感文化”:
实践理性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原型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而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早在他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中,便已形成了。
其说认为,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 以及以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 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虽历经阶级的分野与时代的变迁,它却保有其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实用理性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在消灭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灵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于抽象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探索无限的奥秘;而只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在人世快乐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无限。
这种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体与用不二、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据说这个所谓“乐”,还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则,而且是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在中国哲学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是巨大深厚无可抵挡的乐观力量,是人的心理本体,那个最后的实在。
忧乐共同处:认同儒家为根基的民族文化,都追求天人合一
乍一看去,以“忧”“乐”二义统领中国文化,其势当如水火,绝无相容余地。但稍加寻绎,却可看出,两说偏又颇多共同之处。
首先,二者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今天和过去之间构建某种理想的承续关系,以度过时代冲击的震荡,为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命运定立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