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1964年,因“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布罗茨基被定罪为“社会寄生虫”,又于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永不复归。他把苏俄岁月称为“前世”,逃离后的生活唤作“今生”。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布罗茨基终于在威尼斯找到了“西方”的最佳想象,一座建造在冬日海岸边的理想城市。1973年到1989年,布罗茨基曾17次踏入威尼斯城,直到1996年被安葬在圣米凯莱岛公墓,与被他戏谑调侃过的庞德做了永远的邻居。
乡愁与流亡是布罗茨基的永恒主题。布罗茨基注视着威尼斯,如同彼得堡延伸进了一个更好的历史,涣漫出另一个维度的文化乡愁。彼得堡理应在人类文明史上获得更好的名声,“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败坏地理的名声”,而地理必将为想象伸张正义。为了抵御这种重复的败坏,布罗茨基把旅行当做流亡,流亡式的匿名性,带给他的并非是虚无的痛苦,而是自我的自由。
书评人萧轶认为,面对布罗茨基的文字,阅读即翻译,需要在熟悉他的语词规则或隐喻方式的情况下,在从外语翻译过来之后,在中译本上再度进行汉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才能深入布罗茨基的语言内部,挖掘他那些新奇而冷峻的隐喻方向。故而这篇为威尼斯的布罗茨基而作的书评,也有意模拟了《水印》的文风,试图使阅读的过程成为对布罗茨基双眼略过城池的某种效仿:威尼斯如何遭遇布罗茨基,时间如何生产历史,水的波纹容纳了逝去的一切。
受雇于一套明信片的文明
在《悲伤与理智》中的第一篇《战利品》,布罗茨基特别写到了一位姑娘在他过生日时送给他的“一套像手风琴风箱一样连成一串的威尼斯风光明信片”,这套明信片是那位姑娘的奶奶于二战前夕在意大利度蜜月时带回来的,也恰好是在布罗茨基因阅读了两部以威尼斯冬季为背景的小说而常常念叨威尼斯时送来的。这些老旧的明信片让他感觉“几乎就像是在阅读亲戚的书信”,浓郁人文色彩的水城景色让他认为威尼斯呈现出来的气质,如同“做好了应对寒冷季节之准备的文明”,以致于他翻阅了无数遍。在被列斯政权认为是苏俄“寄生虫”的晦暗年代里,它们温暖着他那沉闷漫长的冰冻生活。
对布罗茨基而言,“季节就是隐喻”。冬天是正直的、道德的,是最真实的季节。寒冷是虚无的标准和精神所在,它规避了虚伪而战胜了人类,因为冬季色彩最为贫乏,所以最为诚实。再者,道德的诚实和欲望的贫乏,给现实世界的人类活动带来无边的恐惧,这是我们与时间保持类似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些冬天风景的明信片上,他想象着苏俄社会极力批评的西方社会,如同吊袜带的暗示力量,这些明信片风景散发着奴性的芬芳,诱惑着逃离的心脏。布罗茨基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若能步出国门,一定要在冬季前往威尼斯,我要租一间房,是贴着地面的一楼,不,是贴着水面,我要坐在那里,写上两三首哀歌,在潮湿的地面掐灭我的烟头,那烟头会发出一阵嘶嘶的响声;等钱快要花光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购返程票,而要买一把手枪,打穿我的脑袋。”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受雇于明信片想象所产生的颓废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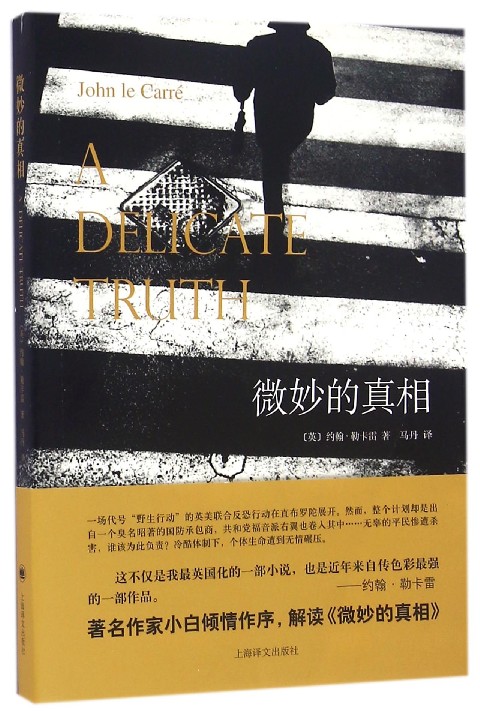
《水印——魂系威尼斯》
命运垂青于这位以写诗为理由而反抗社会主义必须劳动的诗人,让他得到西方名人的呼吁与营救,安全离开了那个国度,不仅时常到威尼斯去,还在水面上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在那本关于威尼斯札记的《水印:魂系威尼斯》里,布罗茨基如同给那位姑娘写情书那般,用情色意味的调侃方式,借助跳跃的思维和宽阔的比喻,如同面对某种危险的愉悦,鲜明而刻意地警惕着情感泛滥的叙事病灶,语言密度无限爆炸似的表达着深沉潜藏的忠诚与喜爱。写下威尼斯无数倒影的他,最终让自己也成为威尼斯的一道水印,他对威尼斯的热爱和写下的诗文让他青史留名,如同“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中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竖立在威尼斯游客们的心底。他也长眠于威尼斯墓岛,尽管与被他戏谑调侃过的庞德做了永远的邻居。而这本关于威尼斯的书,成了他销量最大、译本最多的散文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