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以战争始,以战争终。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仓皇、离乱,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上海则稍有不同,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战火与动荡,于神州板荡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于难,而且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魏斐德语)。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在这段史上最黑暗最艰辛的可怕岁月中,上海城市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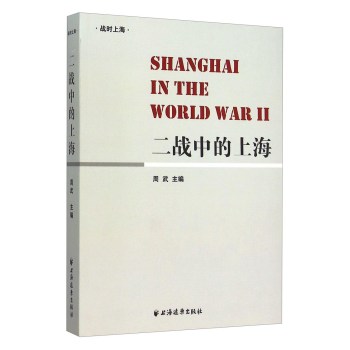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强劲旺健的城市活力和发展态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更因缘际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艺术、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研究,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当年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出版业的图书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于此可见一斑。其实,不仅商务印书馆和出版业,上海的贸易、航运、金融、工商业、房地产、信息等行业也都步人各自的“黄金时代”。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黄金时代”因此被终结。
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地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像“森林中的生灵逃避天降大祸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仅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落脚之处,几乎每个角落都挤满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仓库,甚至棺材店。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单1937年岁末处理的尸体即多达101,000具。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被难情形最惨不忍睹。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战前最繁盛的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另据统计,闸北华界地区全毁于“八一三”事变的里弄即达295条。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和“自治模范区”,被誉为中国迈向工业时代的一面旗帜,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毁厂房,内存铁质器具,上自构造复杂之大机器,下至零件,甚至连虹口招商码头等堆栈地上铺的铁板,皆被敌人撬走了”。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