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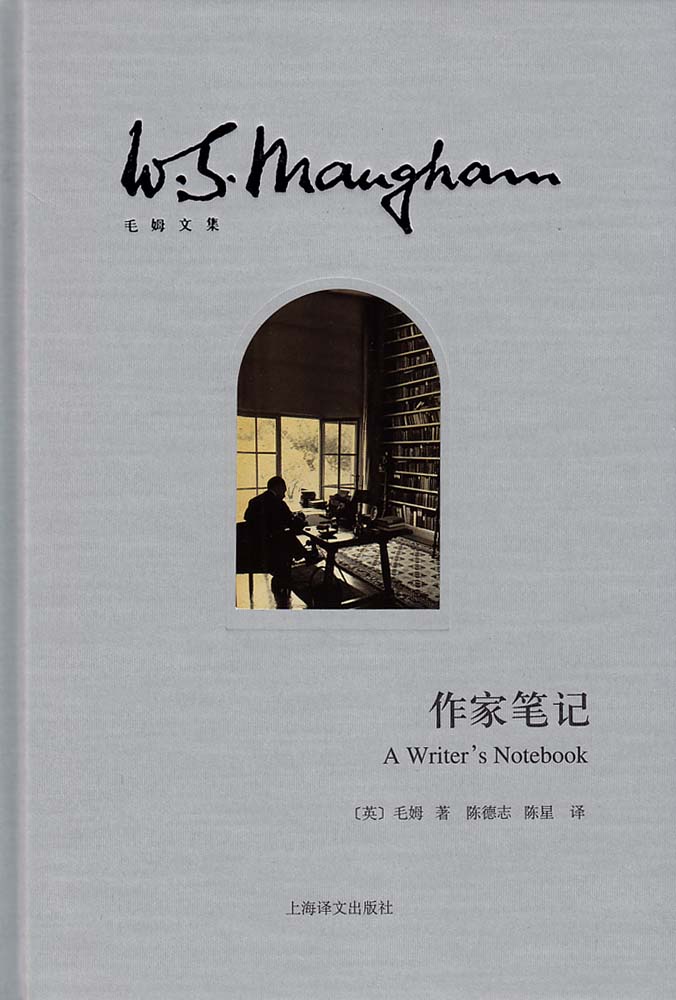 毛姆的文字极具魅力,但是这种魅力不是通过华美的文笔,不是通过议论,不是通过冷嘲热讽而形成的,那是一种经过了长时期游历生活的浸淫,对真实生活与虚构作品的认知愈发敏感的缘故。 毛姆的文字极具魅力,但是这种魅力不是通过华美的文笔,不是通过议论,不是通过冷嘲热讽而形成的,那是一种经过了长时期游历生活的浸淫,对真实生活与虚构作品的认知愈发敏感的缘故。
毛姆写到一个段子:一位贵夫人也想让自己儿子成为作家,因此询问毛姆的意见。他回答说:“每年给他一百五十镑,给五年,叫他见鬼去吧。”这样的回答原本就戏谑的成分大一些,当不得真。但是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愈发觉得这个答案之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挨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须精打细算,品尝生活的多种面向;他不至于陷入贫困,但为了衣食住行需要时刻辗转于各种工作之间。总之,“一个作家就应该尽量地让自己身处合适的环境,能经历人世的荣枯变迁。他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需要什么事儿都做一点”。这也许就是《作家笔记》的由来,基本涵盖了毛姆的一生,从十八岁到七十岁,我们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乃至成熟的历程,也见证了时光倏忽之间把一个毛躁的医院实习生变成一个絮叨的耄耋老人。这种人生的感喟就浓缩在这短短几百页的文字当中,作家以笔记的形式,传递出的仿佛是传记熟悉的影子。
也许,我首先应该澄清一下《作家笔记》并非如我之前所料想的,是那种写满了各种八卦传闻,作家逸事的段子大全。毛姆也并非如同尼采或者帕斯卡尔的书写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各种警句格言,以备让后人获得一种振聋发聩式的宗教体验。顾名思义,作家笔记就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的文字,短则几个字,多则千余字,自缀成文,散乱成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毛姆的一生极其丰富多彩,少年从医,又弃医从文,参加过一战,做过间谍,游历过世界各地,上世纪20年代还来过中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字和记忆,这些在《作家笔记》中都有清晰而直观的记录和描述。当然,毛姆的笔记是那种典型的小说家言,“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地观察人”。所以本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都是对各个行当的各色人等细致入微的描述。身为作家的毛姆并不擅长议论人事,臧否是非,他固然能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诠释出人性的各种特质,或高尚伟大,或卑微渺小,或懦弱低劣,但是一旦涉及到各种道德评价和具体的评点,毛姆的书写就开始陷入平庸的笔调,而且充满各种偏见,尤其对很多女性的评价尤其鄙视,让我辈读之,颇感意外。
其实很难区分《作家笔记》的几种题材,因为毛姆是按照年份,而不是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的书写。但是我的阅读印象,大体上还能作出分类,比如对宗教、对女人、对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观察、对各种人物的描慕,对写作素材的提炼,对世界各地风景的描写。上面我提到说,毛姆很擅长观察人物,描述风景,这两者在《作家笔记》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方面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1917年,他去俄罗斯执行情报部门的秘密任务时,特意去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对这位俄罗斯文学史上描写苦难灵魂最为深刻的大作家的描述,让我一读难忘:“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尽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我得承认,仅读这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就已经胜似毛姆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对其作品的评价。对许多小说家而言,描写人物的外貌是最为棘手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是一本正经的列清单,鼻子眉毛眼,一笔笔描述刻画,力求完整清晰。但是这种古典主义的写法在现在已经不再实用,因为现代以来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孕育出的文化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文化,要求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简单而直接,甚至可以省略。但是这种简约同样遭到了毛姆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写意的手法,完全忽略了客观事实,只注重作者写作时的愉悦,但归根结底无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有一些作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外貌特征有多重要。他们似乎从未发现人物体态特征对人物性格有多大的影响”。而通过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似乎领略到毛姆的写作手法,那是一种具体的简约,注重细节的刻画,但从不在某个相貌特征上浪费过多笔墨,画龙点睛般的笔法,简单清晰,而且人物特征突出鲜明。我们能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完整领略到毛姆的这种描形慕物的文字魅力。此时的描述不过是管中窥豹,用他点评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契科夫的文字形容就是一种“指缝间的风景”:“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