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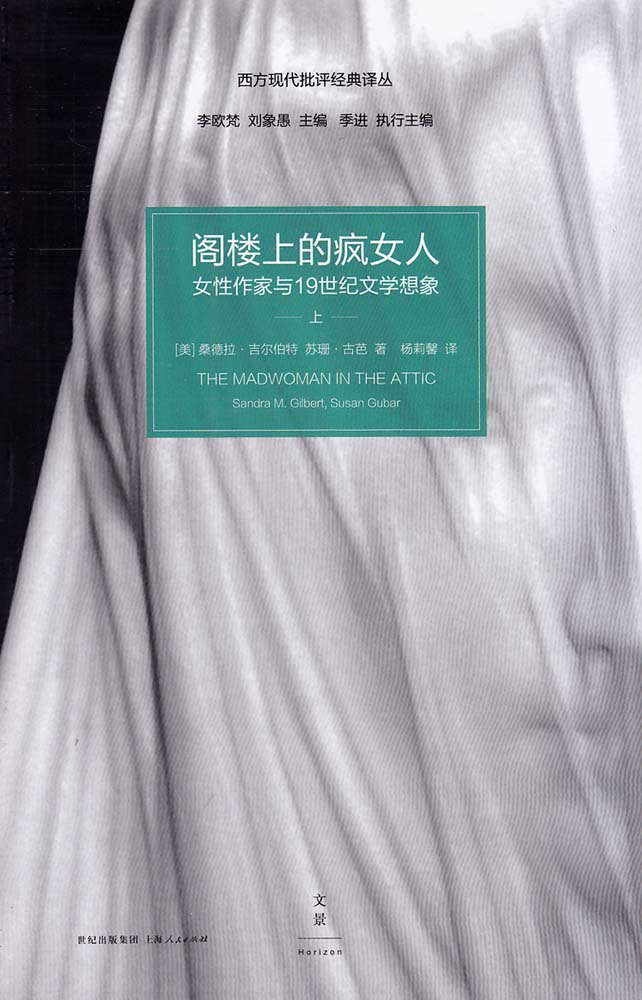 人生而有性别之分,从何时起,“性别”一词除了描述我们生而有之的类别外,还有了其他意义:性别认同、性别主义、性别歧视……身为女人或身为男人,对我们的身体、生活、经验乃至思考方式有何不同的塑造与影响?我们又是从何时开始察觉到这两种(或者多种?)不同? 人生而有性别之分,从何时起,“性别”一词除了描述我们生而有之的类别外,还有了其他意义:性别认同、性别主义、性别歧视……身为女人或身为男人,对我们的身体、生活、经验乃至思考方式有何不同的塑造与影响?我们又是从何时开始察觉到这两种(或者多种?)不同?
6月6日在北京雨枫书馆·百盛馆,世纪文景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孙柏副教授,为读者讲授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的基本历史、观点与关怀,并分享他们自己的“性别意识开窍时刻”。本来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场地来了两百多人,有不少读者只能站着或坐在地毯上听完全程。这场关于女性主义、女性写作话题的对谈,因为两位不同性别嘉宾的精彩讲解,现场讨论格外热烈,更引发很多当下热门话题的深度讨论和思考。在戴锦华看来,当下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与历史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场对谈围绕“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最新作品《阁楼上的疯女人》展开。《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是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创始人之一,堪称“学术界的疯女人”。她们长期合作,撰写了多部女权主义批评论著。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她们认为,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柏介绍称,《阁楼上的疯女人》从它在英语学界问世,已经有超过35年时间了。戴锦华说道:“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是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戴锦华认为,当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回顾35年前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当年)非常没有资历的两个女教授,在英文系撰写了这样的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痕迹。”而这部“经典”的作者“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同的特征”。戴锦华坦言,“我想这本书会开启一个性别思考”,而这种思考是“(在)我们更加自觉的中国主体位置上跟西方的对话。”
除了关于“性别的思考”,这本关于19世纪女性文学的著作还引发了戴锦华“重新体认今天我们所置身的历史状态和文化状态”。她说:“大概一年前我看到网上一个有趣的帖子,大概意思是网络禁忌,在网上切忌不能干什么,第一句话叫做‘猫狗是主人’,第二句话叫做‘同志不能黑’,第三句话叫做‘直男癌去死’,中间有两句话都是性别议题,而且如此开放,如此先锋。”而和这种“先锋”“前卫”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基于当下这种“先锋”与“前卫”的观念对历史的看法。戴锦华说:“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今天已经有了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么’?而严肃的说法是,《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当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感知和体认后),我们再返回来看《简·爱》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造成这种不同)有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勃朗特赋予《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种东西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的昂扬和进步。但是同时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殖民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