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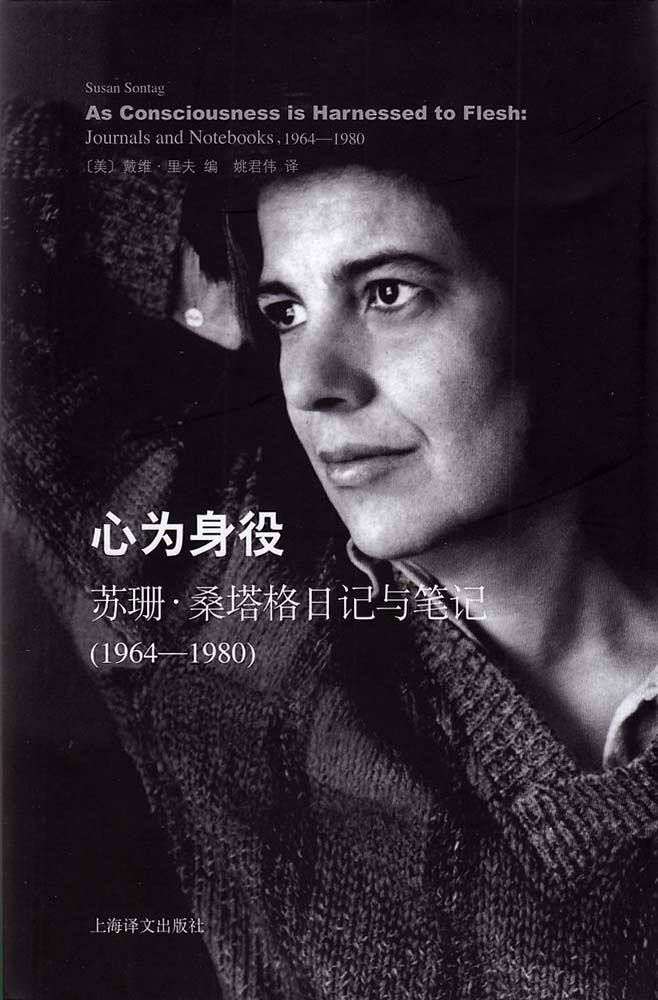 1968年春,SS(即苏珊·桑塔格)应北越政府之邀,作为美国反战积极分子代表团成员,访问北越两周(5月3日—17日)——此行引起了广泛争议,也为她同年出版的《河内之行》一书奠定了基础。通常,这些笔记要么是东道主告诉她的事情的文字记录(我没有找到SS对听到的东西所做的评注,不管是肯定还是质疑;这些笔记本更像是一个记者的,而非一个评论家的),要么是日程安排,以及,SS几乎永远如此,她对访问的地方做依据事实和历史的评注,同时还列了越语单词表及其英语意思。因此,我只选了些代表性条目编录在这里,而完整地引用我能够找到的那个更带有回顾性的、质疑的和分析的条目。的确,该条目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其他条目,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比《河内之行》都更有自我意识。 1968年春,SS(即苏珊·桑塔格)应北越政府之邀,作为美国反战积极分子代表团成员,访问北越两周(5月3日—17日)——此行引起了广泛争议,也为她同年出版的《河内之行》一书奠定了基础。通常,这些笔记要么是东道主告诉她的事情的文字记录(我没有找到SS对听到的东西所做的评注,不管是肯定还是质疑;这些笔记本更像是一个记者的,而非一个评论家的),要么是日程安排,以及,SS几乎永远如此,她对访问的地方做依据事实和历史的评注,同时还列了越语单词表及其英语意思。因此,我只选了些代表性条目编录在这里,而完整地引用我能够找到的那个更带有回顾性的、质疑的和分析的条目。的确,该条目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其他条目,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比《河内之行》都更有自我意识。
[未标明日期,5月,但很可能是5月5日或6日在河内。]
文化差异是最难懂、最难克服的东西。“moeurs”[“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差异。(有多少是亚洲的,又有多少是越南特有的,我在第一次亚洲之行中当然分辨不出来。)对待客人、陌生人、外国人、敌人的不同方式。与语言不同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即我说的已经慢下来而且简化了的话是由一个翻译转达出去的,不然,如果我对他们说英语,那我们就是在说儿语。
此外,还有一难,即被降为孩子的状态:被安排好,被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有人向你解释,有人为你担忧,对你呵护有加,让你身处监管之下。我们一个个成了孩子——更加令人恼火的是,一群孩子。他们是我们的保姆,我们的老师。我努力去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不同(莺、贤、范、全。越南名字,原文分别为Oanh,Hien,Pham和Toan。),我担心他们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同或者特别。我感觉我自己一直试图讨好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我以一个聪明、彬彬有礼、愿意配合、容易辨认的样子出现。
第一印象是每人说话的风格都一样,说的内容也一样。这一点又因为好客的礼节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套话而得到了强化。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一张矮桌子,几把椅子。我们握了一圈手,然后坐下。桌子上:两只盘子里装了烂了一半的青香蕉、香烟、未烤透的饼干,还有一碟子纸包的中国糖果,几只茶杯。我们被介绍给大家。他们的领导看着我们。“Cac ban…”[越语“欢迎”]有个人掀开门帘进来,开始上茶。
头几天好像是很没希望了。存在一道似乎无法跨越的障碍。感觉他们有多么奇异——对我们而言不可能把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理解他们,他们显然也不可能理解我们。一种不可否认的高他们一等的感觉;我能理解他们(如果不将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除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感觉我的意识包括他们的,或者能够包括——但是,他们的绝对包括不了我的。我绝望地认为,我迷失在我最钦佩的东西之中。我的意识太复杂,它知道大量各种各样的乐事。我想起[贝尔纳多·]贝托鲁奇[1964年]的电影[《革命前夕》]中的格言——“没有在革命前生活过的人绝对没有品尝过生活的甜美”——跟安迪[美国作家、活动家安德鲁·科普坎德]提了。他同意。
不只是没有希望。还是一种煎熬。当然,我此行并不懊悔。这是一种职责——一次政治行为,一出政治剧。他们在扮演他们的角色。我们(我)必须扮演我们的(我的)角色。它的沉重在于脚本完全是他们写的这一事实;而且他们也在导这出戏。我认为没问题,应该如此。但我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履行职责而已。而且内心里我非常伤心。因为这意味着我无法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任何东西——一个美国革命者无法从越南革命中了解到任何东西,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比如)从古巴革命中学到东西的,因为——至少从这个视角看——古巴人和我们很像。
我们有过一种角色:我们是越南战斗的美国朋友。一个共同身份。河内之行是一种酬答,一种惠顾。我们在受到一次款待——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受到答谢——然后,我们将会被送回国,带着加固了的忠诚,去继续做出我们认为合适的各自的努力。
当然,在这一共同身份中有一种微妙的礼貌。没人要求我们——单独或一起——证明我们有理由应得这次旅行机会。我们被邀请和我们愿意来似乎是一拍即合。我们每个人做我们能做之事——这像是默认的。没有人问我们特别或具体为这场战斗做什么。没有人要求我们解释——更别提去证明——我们的努力的水准、质量和策略。我们全都“受欢迎”。
人人都说:“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只有美国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从一开始,我就想怒吼。我尊重他们态度的高尚,但我怜悯他们的天真。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在说的话吗?难道他们对美国一点都不了解吗?我总有点认为他们是小孩——漂亮、天真、固执的小孩。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尽管这出戏要求我扮演一个小孩的角色。
我渴望我所生活的这个立体的、有质感的成人世界——即使是在我正在访问的道德童话构成的平面世界里处理我的(他们的)事情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