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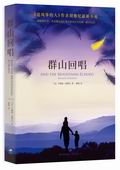 喜爱读书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胡塞尼,在出版了《追风筝的人》与《灿烂千阳》之后,卡勒德·胡塞尼就成为了阿富汗的代言人,尽管作者本人对这样标签化的称谓不以为然。胡塞尼笔下的故事虽然与阿富汗战争密切相关,但在早早离开那片被战火和贫穷肆虐的故土之后,作者更想表达的是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与抗争。或许正是基于此,胡塞尼在新作《群山回响》的宏大叙事中一反之前的常态,弱化了战争场景,更注重亲情和复杂的家族关系的描绘。书中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开篇,千丝万缕的人物关系总能让相关的情节随着线索徐徐展开,每一个被束缚其中的角色构成阴暗真实但绝不波澜壮阔的故事。 喜爱读书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胡塞尼,在出版了《追风筝的人》与《灿烂千阳》之后,卡勒德·胡塞尼就成为了阿富汗的代言人,尽管作者本人对这样标签化的称谓不以为然。胡塞尼笔下的故事虽然与阿富汗战争密切相关,但在早早离开那片被战火和贫穷肆虐的故土之后,作者更想表达的是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与抗争。或许正是基于此,胡塞尼在新作《群山回响》的宏大叙事中一反之前的常态,弱化了战争场景,更注重亲情和复杂的家族关系的描绘。书中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开篇,千丝万缕的人物关系总能让相关的情节随着线索徐徐展开,每一个被束缚其中的角色构成阴暗真实但绝不波澜壮阔的故事。
小说以一个波斯民间故事开始,寓言中父亲对女儿的温情讲述,让初读之下的读者误以为是一则童话故事而颇感惊异。那么接下来的叙述却更加触动人心,因为以童话开篇的故事竟然如此残酷和真实。作者虽然摈弃了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将叙述重心置于普通人的呐喊与挣扎,却并未削减“阿富汗民族的变迁在人们心中烙下的伤痛”这一主旨。应该说,胡塞尼放弃了描绘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战乱生活,转而以个人化的抗争方式去展现人物命运的逃离与缺失。
《群山回唱》由一个极富悲剧色彩的童话故事开篇,残忍与仁慈只是一体两面,这种表现手法似乎和余华的小说《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活着》相似的是,胡塞尼以帕丽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展开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巨幅拼图。然而在具体的故事推进却与《活着》迥然不同,多线并进的方式将不同人物的故事线梳理开来,而又彼此扯不断。每个人物都是一片碎片,要亲自填补到属于自己的空缺里,才会形成生命的完整。那些迷离在记忆里的情节,从别人的嘴里还原你看不见的另一面。如果不了解作者这样的写作意图,《群山回唱》蛛丝网结式的人物故事会让读者觉得枝丫漫散,歧路重重。其实,这和我们的生活相似,个人通过家庭这个基本细胞存在于世界大机体中,细胞与细胞之间结合,碰撞,渗透,衍生出人与人之间或近或远的联系;牵绊,纠缠,生发出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在地域、战争、生死、别离、承诺与谎言里穿行,最终盘扣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闭合的圆圈,人生在世便是相逢。
有关小说主题,胡塞尼这样说道:“《群山回唱》这书的写作始于家庭这概念。事实上,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家庭。抛开了家庭这个线索,你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无法理解周围的人,无法弄明白整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胡塞尼笔下阿富汗的家庭和人民,他们渺小、贫穷、苦难,轻似鸿毛,然而最终还是这些平凡却真挚的东西打动了读者。可以说,《群山回唱》里讲了不止一个故事:阿卜杜拉的故事、舅舅纳比的故事、继母帕尔瓦娜的故事,甚至是义工的故事。胡塞尼的故事没有绮丽的异国风情,也不以复杂、奇诡的剧情取胜,更与宏观大局无关,打动人心的是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真情实感。可以说,《群山回唱》给读者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故事巧妙的设计,而是其中包含的更深层的意义。
胡塞尼在用克制的情绪书写,他试图还原生活的真实。本书不像《追风筝的人》,并没有对那些黑暗日子的直接描写。尽管如此,“苦难”仍是小说唯一的关键词,“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然而胡塞尼却用一个又一个故事努力去消解这种苦难,作者正是在苦难中看到人性的恶,看到人性的善,看到那些人们的内心挣扎,看到人们被隐藏的过去,看到他们的付出与牺牲,人间百态,均汇于此,是以,这虽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也可以用“牺牲”和“爱”去消解全部。
如同故事中的帕丽终于找到了离散多年的哥哥阿卜杜拉,弥补了双方人生的缺口;帕丽兄妹的继母帕尔瓦娜和自己的孪生姐妹马苏玛,尽管有过嫉妒和伤害,双方还是为彼此互相牺牲和成全;兄妹俩的舅舅纳比,夹在对主人妻子的单相思和主人对他默默的同性之爱中,明白了爱和责任的真谛。
读罢《群山回唱》,给读者最大的感受便是感受到了书中人物那种对于命运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似乎又合情合理,因为妥协之后展现给人们的是另一种生活面貌,一种让人不会时常带有怨言的生活状态,对于普通人,这一切又显得多么来之不易。那么,这种妥协,抑或这种自我的宽恕,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