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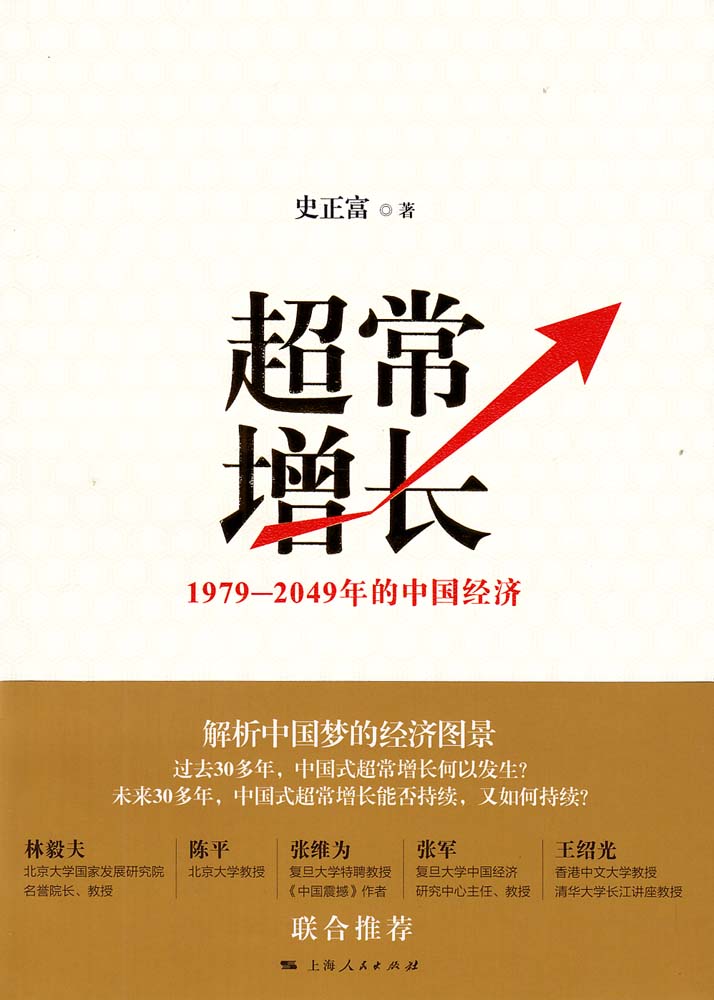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不仅重绘了世界经济政治的版图,也正在促使人们对西方历史经验所确立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把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发展的成功归功于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史正富教授的新著《超常增长》是这一观点的特具代表性和独创性的论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不仅重绘了世界经济政治的版图,也正在促使人们对西方历史经验所确立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把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发展的成功归功于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史正富教授的新著《超常增长》是这一观点的特具代表性和独创性的论著。
这本书强调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并提炼出三维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理论来解读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功的秘密。这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视角。
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当代经济问题,但是有非常强的历史感。书中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解释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帮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历史。反过来说,这本书为理解现实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纬度。虽然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中国数千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一统天下的情况来看,地方分权的做法似乎都找不到历史的路径依赖,但从中国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深入观察的话,以地方分权为重要推动的改革,其成功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我们知道,自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以来,除了魏晋南北朝和五代这两个分裂时期外,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在这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代表地方利益的独立的地方政府的位置,所有的地方行政机构,不论是州县还是行省,都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已。所有地方官员都只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在地方施政的主要职责就是所谓刑名钱谷,也即地方的稳定和上缴中央的赋税收入。而这两者也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基本指标。
在这种制度下的地方行政架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被称之为“郡县”,而与“封建”相对立。两千多年来,除了那些分裂时期外,被郡县制所框定和局限的中国地方很少有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和空间。郡县制把所有的权力、资源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是为了实现中央的施政目标而存在,它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目标,也不允许有这样的目标。当然,即便它有这样的目标,它也没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资源和手段。
郡县制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它帮助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局面(这一“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避免了地方封建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乱与纷争。但是郡县制的弊端也很明显,它剥夺了地方发展的机会,窒息了地方发展的活力,而这恰恰是它的对立面“封建”所能给予地方的。所谓封建,是相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地方分权自治的制度安排。这种体制安排以保护和促进本地利益为最大诉求,但对大一统的帝制来说则是离心分裂的力量。于是郡县所强调的政治统一和封建所追求的地方利益始终是中国历史上冲突对立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关于“封建”和“郡县”的是非优劣之争因此长期以来主导了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张,就是要把(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封建)结合到中央集权(郡县)的框架之中。顾炎武相信把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优点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天下的有效治理。他认为即使圣人再世其所能做的也是如此。
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在中国出现。民国时期曾经有过短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但是因为抗日战争和内战,这样的分权并没有真正实现。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独立的财权和事权,可以代表地方利益来谋求地方发展。这个改革实际上释放出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被压抑的地方发展的潜能,使其史无前例地爆发出来。如史正富在书中所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实现“超常增长”其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里,来自于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而进行的持续而激烈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