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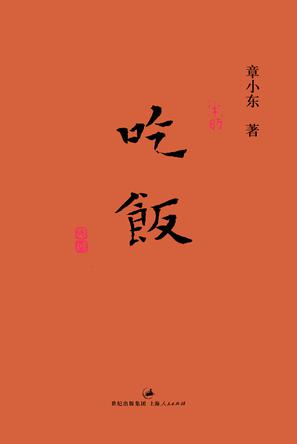 她不懂的是,不仅让人吃饱饭的,更让人抬起头来思考自己和社会关系的地方,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伊登”。也许还得多吃几代饱饭,我们才能最终超越那些有关伊甸园的贫瘠想象。 她不懂的是,不仅让人吃饱饭的,更让人抬起头来思考自己和社会关系的地方,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伊登”。也许还得多吃几代饱饭,我们才能最终超越那些有关伊甸园的贫瘠想象。
对中国人来说,“吃饭”始终是最大的问题,是萦绕在统治者和老百姓心中最长久的噩梦。如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百姓就要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继而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统治者也就坐不稳江山。所以,大凡政治家和文学家给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勾勒的桃花源,无非都是能吃饱饭的景象罢了。无论是孟子见梁惠王的“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还是《红楼梦》中黛玉替宝玉做的颂圣诗中的“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抑或是大跃进时期让社员们敞开肚皮吃的公社食堂等等,都无一例外。
作者章小东在文中多次提及“伊登”,也就是上海话中的“伊甸”。她千里迢迢赴美,就是认为美国是一个人人可以吃饱饭的“伊登乐园”。这也许也是所有那一代刚刚走出国门的人,对于伊甸园的贫瘠想象吧。到了美国之后她发现,这里满足了她的一半想象,人们完全不用忧虑食物的匮乏,然而另一半的情况是,不劳者不得食,艰辛的吃饭故事依然在不间断上演。
曾经深居闺中的上海小姐也不得不挽起袖子到餐馆打工,每小时只有4美元的工资;一个内地来的学生在送披萨的途中撞上一棵大树,前车盖上还有一块从他嘴巴里喷出来的、没有来得及吞咽下去的带血馒头……尽管再也没有饿过肚子,可是对饥饿的恐惧依然如影随形,章小东写到自己一定要把冰箱和食品柜塞得满满当当的才有安全感,在胆结石发病要做手术的关头,她还溜回家做了一顿海鲜菜泡饭,坚决不要当“饿死鬼”。超市里西瓜降价到99美分一个,她一口气买了20个,全家人天天吃西瓜,吃到后来都烂在地摊上,臭气熏天。她用轻快的笔触娓娓道来这些逸闻趣事,读来却是笑中带泪,颇觉苦涩。
无怪乎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要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冠上一个通俗的名字“吃饭哲学”,贯穿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智慧,其实就是在不断地找寻百姓和“吃多少饭”之间关系的平衡。很少有人思考过,为何以平原地势为主的中华大地,却始终盘旋着饥饿的阴影,饿肚子的恐惧一代代传承下来,几欲成为烙印在骨子里的DNA。
只有始终保持着民众对饥饿的恐惧,才能保证他们可以为了吃饭放弃所谓的道德和尊严。书中写到蹲了20多年大牢的大右派毕芦,如果有人叫他大名他就会条件反射的跳起来,给你来个立正,大叫一声“有!”70多岁的人了,每周一次到孤儿院做义工劳动两个小时,报酬是可以把孤儿们吃剩的饭拿回家。作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背着一个巨大的垃圾袋撞进办公室,打开口袋一口气吃了五盒蛋炒饭。章小东不禁感叹:“吃饭实在是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为了吃饭许多人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我不也是违背了自己吗?”
吃饭的确日常生活头等大事,然而视野里若只有吃饭,必将难逃精神上的庸俗化与市侩化。作者记叙自己工作的公司因为911的影响大幅裁员,可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老板依然号召大家多多支持快要倒闭的老牌商店K百货,她却想自身难保还要去帮助别人,真是天真的美国人做派;看到有同事在总统大选期间义务为演讲中心维持秩序,就认为他不过是想过把指挥别人的瘾,宣泄下底层小职员的压力罢了。她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口中的“民主、自由、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她只能用她的吃饭哲学将一切功利化。
她不懂的是,不仅让人吃饱饭的,更让人抬起头来思考自己和社会关系的地方,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伊登”。也许还得多吃几代饱饭,我们才能最终超越那些有关伊甸园的贫瘠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