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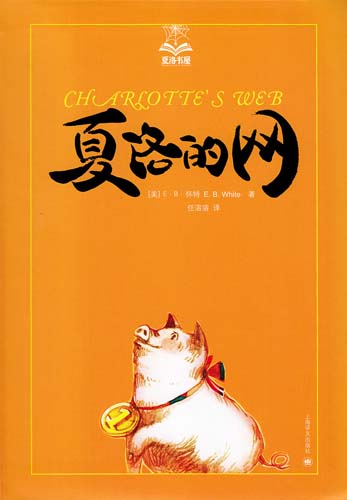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
●“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
●“为了让小朋友和儿童文学作家多看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译啊译,译得越多越好!”
●“我生下来就该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评委们也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向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表达心中由衷的敬意。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从翻译第一篇作品开始,他手中的笔就从未停歇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小飞侠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而任溶溶从事这一事业已经60多年,任溶溶说:“我生下来就该干这一行,这一行也用得着我。”
2013年春节,我曾致电老人,想请他说一点新春寄语,老人说:“我今年九十了,什么都不想了,惦记的惟有儿童文学。我希望儿童文学好。”
“快乐法则”照亮天地大美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任溶溶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出自己名字的秘密——任溶溶这个名字,是他跟女儿借来的。在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之初,他经常需要用到很多笔名,那时恰逢女儿出生,喜不自禁的任溶溶索性将女儿的名字拿来我用,随着署名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任溶溶也成为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
其实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1927年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在广东一待就是10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岭南度过,直到1938年重新回到上海。
任溶溶从小就是个电影迷,“不但是个电影迷,而且是个电影说明书迷”,收集了很多电影说明书。到后来觉得不过瘾,干脆自己创作起电影说明书来。从主要人物到情节设置,从故事大纲到人物台词,小任溶溶写得有模有样。到后来这些自己写出来的电影说明书,竟然贴满了一面墙。虽然读者不多,但这大概算是他最早的创作了吧。除了写电影说明书,任溶溶还画连环画,甚至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写过《济公传》的续集,并像模像样地投给报馆,虽然最后石沉大海,但是这样的尝试让任溶溶收获到创作的快乐。孩童的游戏里常常蕴藏着才能的种子,也孕育着创作的萌芽。
童年是一个作家重要的创作母题,同时也是作家汲取灵感的不竭源泉,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童年的经历就显得更为重要。童话大师林格伦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她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任溶溶也曾说过:“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为孩子写作首先当然应该熟悉孩子,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想法。怎么熟悉孩子呢?就要和孩子交朋友,跟家里的孩子交朋友,跟周围的孩子交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成为他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尽的文学宝库。
追溯起来,任溶溶真正与儿童文学结缘其实有些偶然。大学毕业后,他的一个同学在儿童书局编儿童杂志,知道他懂翻译,于是把他拉来翻译一些国外的儿童文学。任溶溶立即被这种好玩的文学以及书中丰富多彩的插图迷住了,作品一篇接着一篇翻,从此一发不可收。
但其实任溶溶与儿童文学的结合实属必然,一旦相遇,终生不弃,风雨几十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儿童文学。甚至在10年浩劫的时候,任溶溶也舍不得放下他心爱的儿童文学。1968年,任溶溶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夏克”而受到批判,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虽然身陷逆境,任溶溶在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打倒,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为了能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他早就准备好意大利文的教科书和字典,只是一直抽不出时间学习。到了“文革”,被赶入牛棚,正好有大把的时间,于是他重又把学习意大利语的书籍捡起来开始自学。他还买了本意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学得津津有味,并在写“交代”和“检查”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意语单词和文法规则。“文革”10年,他不仅学习了意大利文,还自学了日文。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