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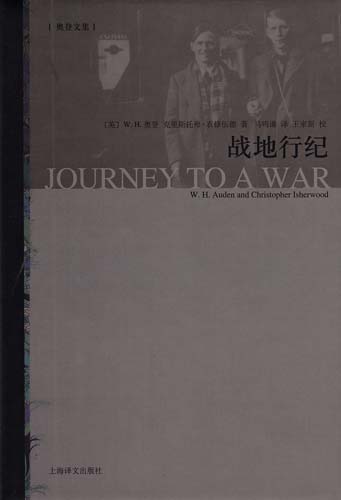 周克希先生在他的随笔《译边草》的“译余偶拾”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过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翻译和演奏有相通之处。演奏者面对谱纸上的音符,演奏的却是他对一个个乐句,对整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他要意会作曲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加上他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 周克希先生在他的随笔《译边草》的“译余偶拾”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过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翻译和演奏有相通之处。演奏者面对谱纸上的音符,演奏的却是他对一个个乐句,对整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他要意会作曲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加上他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
看,他说的是“演奏”!
读到这段文字前,我一直在寻找形容译者身份的恰切比喻:炼金术士,雕塑家,还是奥登所说的染匠?似乎都不对。当然,我们常把翻译说成是架设在语言巴别塔上的桥梁,这样譬喻确实通俗易解,大致也吻合贴切;不够处是只粗略说明了翻译的现实功用,而且,桥梁之喻还是个静态的“死”的描述,并不怎么招人喜欢。原文和译文(原作者和译者)分处了两种异质的语言,本就存在着母体和分体、本文和诠释的天然分别;它更与原作者和译者个人的禀赋气质直接相关,而但凡充满个性色彩的语言,其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那些内在的情感脉动,那些幽隐表达的诗意哲理,仿佛是私密性的呓语,微妙而不可捕捉。
真是入道者语,周先生打的这个乐谱和演奏者的比方,恰能说明两者之间神秘而动态的关联。
对我而言,《战地行纪》其实是入手翻译奥登诗歌途中所遇的第一站。
衣修伍德撰写的旅行记部分,虽然行文充满了英式炫技,从句套着从句,也藏了不少机关,但散文的处理余地毕竟宽展些,终究还不难对付,难就难在奥登诗歌的翻译上。奥登的诗作素以诗律的多变和高度的智性为特色,对汉语译者来说,他的诗作堪称是极难演绎的一份乐谱。要演奏好它,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很容易就在尝试的陡坡上跌落下来,连带着母语的词句也会跟着一同分崩离析。
是的,如同一个只会拉肖邦小夜曲的琴手,非要硬着头皮,拿拉赫玛尼诺夫那首繁复的《科雷利主题变奏曲》来试试自己的身手一样,这次,我遭遇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演奏任务。
奥登诗歌的翻译,是一字一词的斟酌、是通篇音准的调适,是穷尽母语可能性的锤炼。有那么多的日日夜夜,我陷身在这个双重的语言困境中,只为得到更妥帖的译法而费尽思虑。有时,走在路上也会左思右想:那里,是不是换个词更准确些?这里,语调似乎还不够顺畅。奥登的诗,真是折磨人的智能和神经。
譬如《从伦敦到香港》的六首诗中,开头《航海记》的头段就很折腾人,原文是这样的:
Where does this journey look which the watcher upon the quay,
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 so bitterly envies,
As the mountains swim away with slow calm strokes
And the gulls abandon their vow? Does it promise a juster life?
最终出现在《战地行纪》中的是这个版本:
这个旅程朝向何方?码头上的守望者
站在他的灾星下,如此地嫉恨艳羡,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正的生活?
让人纠结的是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这个短句。字面意思看似简单得很,可是,译成“站在他的灾星下”总觉得会引发阅读的歧义。读者或会问:“那么,哪颗星才是灾星呢?守望者的灾星是实在的天象,还是个比喻?如果是个比喻,那么好,灾星不就等于说一个人的厄运嘛,Standing under his evil star可不可以翻成‘他霉运临头’呢?”再者,Stand under除了表位置状态,也有“忍受”和“俯首听命于……”的意思呢。
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这么理解呢?我也屡屡这么自问,着实伤透了脑筋。这句的处理,曾先后调试过好几个版本,譬如底下这个:
这个旅程朝向何方?码头上的守望者
忍受着他的厄运,如此地羡慕嫉恨;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平的生活?
另一个纠结落在了Where does this journey look which的从句关系上面:which指代的是journey( 旅程)吗?这个充满嫉恨的守望者是后文那个隐身的主人公——第三人称的“他”,还是码头上某位眺望中的“他者”?遍寻后续诗节,找不出一点可资援引的证据,真是难以决断。
于是诞生了第三个版本(其实,之前就已否定了近十个不成熟版本):
这个旅程已至何处?码头上的守望者
忍受着他的厄运,如此地羡慕嫉恨;
此时群山不疾不徐地划开水面渐行渐远,
鸥鸟也弃绝其誓言。它预示着更公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