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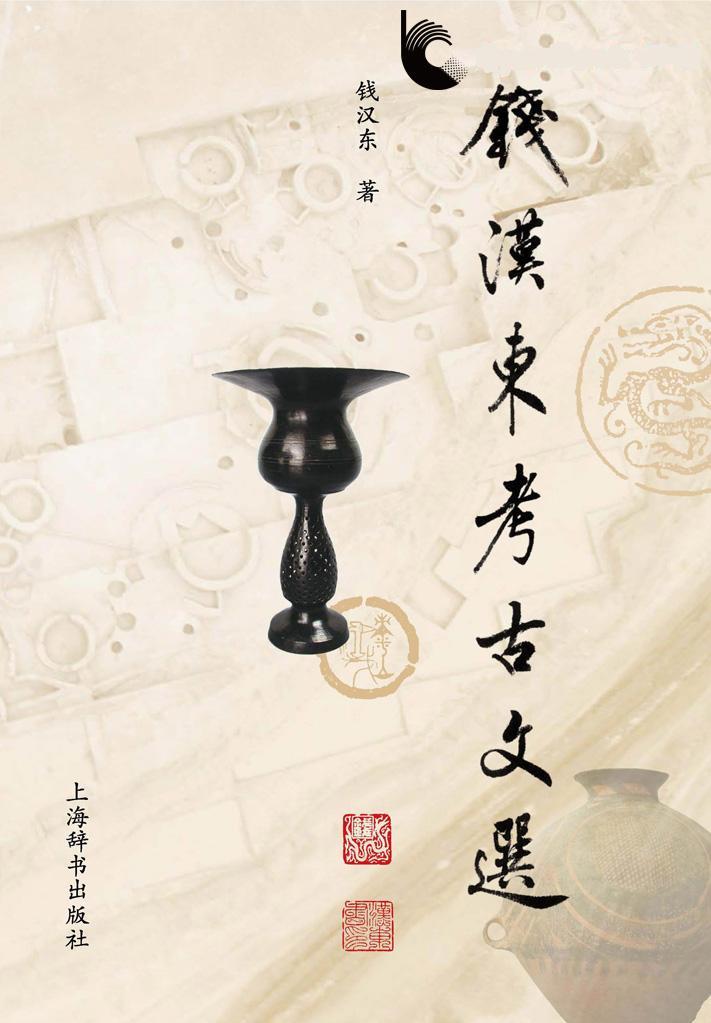 与钱汉东君结识多年,知他在做着分量不轻的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乐此不疲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志业:考古研究。那最初是从古玩收藏开始的,由收藏而把玩,由把玩而探究,再由器物探究进而作遗址古迹的寻访、考察……就这么做着做着,做到了人多视为幽深的“考古”领域。 与钱汉东君结识多年,知他在做着分量不轻的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乐此不疲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志业:考古研究。那最初是从古玩收藏开始的,由收藏而把玩,由把玩而探究,再由器物探究进而作遗址古迹的寻访、考察……就这么做着做着,做到了人多视为幽深的“考古”领域。
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领军人”傅斯年说过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钱汉东作为非专业的考古者,同样亦循此“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准则。动手,从不惜耗资搜求古董器物以把玩研究,到亲至遗址现场动手寻觅古之残遗以辨察求证;动脚,那就更不用说了,光是为了寻访古代名窑,他就曾风尘仆仆,行程二十余万里,遍访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多处古窑遗址。
除了动手、动脚,当然还须动脑,而动脑得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和知识储备——这或可称为学养的内涵 “能量”,正是内涵“能量”的充盈,使他在古物考辨或田野考古时 “钻之弥深”,且每每有独到新异的睿见。然后就是动笔,用晓畅而灵动的文字,将考古文章做得深入浅出,饶有趣味,如此便裨于一般人都能阅读,不致以“考古”为艰深敬而远之。
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当然不错,但并不全面。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接近黄河流域(严格地说是黄河中下游区域)的中原诸国,称为“诸夏”(华夏诸族);中原诸夏之外,谓之夷、蛮、狄、戎,当时受到诸夏的鄙视、防范以至排拒。钱汉东在考古文选《重访三星堆》一篇中说:“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再次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这无疑更合乎历史的事实。八十多年前,傅斯年经考证之后,即指出“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曾被称为“蛮”的长江流域部族先民,同样也是贡献于文化者不少,如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若以更开阔、宏观的视野来看,贡献于中华文明者,还有更多的各部族古代先民。在这本考古文选中,我们看到钱汉东考古足迹所涉之广,除了上述三星堆、良渚遗址外,还有浙江的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桂林甑皮岩遗址,甘肃马家窑遗址,赤峰红山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分布于东西南北,那里的古代先民不同样都曾有贡献于中华文明,因而也同样值得我们满怀崇敬吗?读这些文章,对于中华文明的“其来有自”,以及何以多姿多彩、博大精深,当有更广阔更深切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