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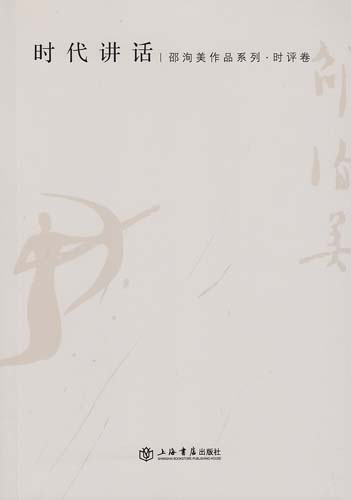 四年前,我们推出的《邵洵美作品集》第一辑五卷,读者品评了他的诗歌《花一般的罪恶》、小说《贵族区》、随笔《不能说谎的职业》和文艺评论《一个人的谈话》,也从回忆录卷《儒林新史》对他的前半生有所了解。当时我们还编制了一份《邵洵美著译年表》。这四年在好些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又收集到成百资料,《邵洵美著译年表》宜作修订。今年这第二辑四卷《一朵朵玫瑰》、《自由谭》、《谈集邮》,收罗的是另一些领域里的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他作为翻译家、出版家、集邮家的才华。人们翻到这一辑的《时代讲话》,或许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别一样的邵洵美。他用笔名郭明写过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文字与其文学作品内容既不同,文笔又相异,难怪跟他同时代的人,包括许多文坛老将也不知情。其实他早有表白:“你须用各种的文体来表现各种题材。我个人就曾经有过这种尝试,而且还认识它的必须。我写诗时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又是一种文体,用了浩文笔名写短篇小说时又是一种文体,写《璫女士》时又是一种文体,用了郭明笔名而为《人言周刊》撰文时又是一种文体……”因为他有很多笔名,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在结集时疏漏;因为用笔名,也就有可能误会而张冠李戴,写文章的郭明的确不只是邵洵美。还有许多他不具名的文章,如孤岛时期为《大英夜报》,每三天写一篇社论,我们无法确认。 四年前,我们推出的《邵洵美作品集》第一辑五卷,读者品评了他的诗歌《花一般的罪恶》、小说《贵族区》、随笔《不能说谎的职业》和文艺评论《一个人的谈话》,也从回忆录卷《儒林新史》对他的前半生有所了解。当时我们还编制了一份《邵洵美著译年表》。这四年在好些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又收集到成百资料,《邵洵美著译年表》宜作修订。今年这第二辑四卷《一朵朵玫瑰》、《自由谭》、《谈集邮》,收罗的是另一些领域里的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他作为翻译家、出版家、集邮家的才华。人们翻到这一辑的《时代讲话》,或许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别一样的邵洵美。他用笔名郭明写过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文字与其文学作品内容既不同,文笔又相异,难怪跟他同时代的人,包括许多文坛老将也不知情。其实他早有表白:“你须用各种的文体来表现各种题材。我个人就曾经有过这种尝试,而且还认识它的必须。我写诗时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又是一种文体,用了浩文笔名写短篇小说时又是一种文体,写《璫女士》时又是一种文体,用了郭明笔名而为《人言周刊》撰文时又是一种文体……”因为他有很多笔名,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在结集时疏漏;因为用笔名,也就有可能误会而张冠李戴,写文章的郭明的确不只是邵洵美。还有许多他不具名的文章,如孤岛时期为《大英夜报》,每三天写一篇社论,我们无法确认。
他说“现在所得到的快乐,完全是我故意逃避了我的环境而得到的”。他不愿跟自己的家族里那些富家子弟一般,依赖祖上留下的遗产过奢靡的生活,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正因为他生于富裕之家,没有柴米之忧,这才可能心无旁骛地读书著文,成为诗人、文学家,这才可能悠然自得地广交文友,出书办刊。他追求美,追求真的文学,向往大办出版事业。可是他无法逃脱命运的嘲弄和时代的打击。战争夺了他的财富,毁了他的事业,可以说,是时代摧残了邵洵美; 然而,时代也造就了邵洵美。因为他处于那个时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正是新文学兴起,期刊出版繁荣,文化艺术硕果累累,才铸就了他的文才,才满足了他的理想。正是当时内忧外患压力下,当政者攘外安内时局混乱,人民生活于不安之中、不平之中,邵洵美跟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忧国忧民,呼吁言论自由,呼吁抗日救国,这才锻炼了他的文笔,这才洋洋洒洒地发表如许耐人赏读的文章。诗人的敏感,以小识大,从国内外时事的变幻中捋出对我国我民的影响,写了这大量的时评政论,企图提请当政者与民众的警觉,有个时期,几乎每周几篇。也正是外侮当前,考验了他的意志,考验了他的人格。对周遭的世界,他始终清醒,他始终坚持做自己:达观,洒脱,幽默,安于清贫,埋头读书;始终恪守自己做人的原则,竭尽一个公民的爱国热诚,保持中国人的气节。在上海孤岛的艰难岁月,他已不再有资本办出版,但心犹不甘,自发担当起抗日宣传的使命,争取外援,出版了中英文姐妹版杂志《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以中国人的气概,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之力,拿起笔做刀枪。
在战前战后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许多编辑随笔里,他假借幽默写时评。但战后的形势令敏感的诗人再也无法容忍,后期一改 《论语》“春秋笔法”的俏皮口吻,换成《人言周刊》严正的笔触。安于现状,安于小百姓生活的邵洵美不能再冷静,不再回避“开口惹出是非来”的风险,他反讽借喻,乃至指名道姓地讽刺,单刀直入地抨击。《论语》的宗旨《论语社同人戒条》在他手里换为《论语征兵歌》。他看透了当官的那套把戏,戳穿表面现象,揭露事实真相。胜利后没有了外患,但国内战火连绵; 国统区内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当局借“动员戡乱”之名,假民主真独裁; 为了镇压革命死乞白赖地争取美援,假装民主学美国,设国代大会,竞选总统,洋相百出;官商勾结百姓吃苦,利用整顿金融,掏空百姓口袋,中饱私囊,等等,他在《编辑随笔》里极尽其讽刺挖苦。
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在《我们的八字》、《过年与分娩》、《夏日炎炎正好眠》、《两个小统计》等文中,明为叹自己的苦经,实际为老百姓抗议。
他压不住心头之火,不再幽默,直言抨击。待人接物一向温文尔雅的邵洵美,笔头却不再饶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混乱中,《论语》 第一六五期编辑随笔《直言谈相》,毫不顾忌地指责“蒋大总统”和其子“蒋督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