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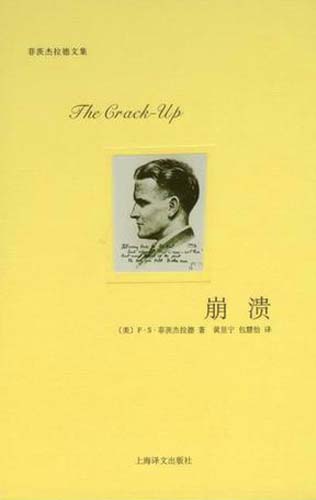 他的句子总是繁复到叮当作响,却还是跟不上自己奔逸的思路,写到最后似乎总欠一点重物坠住整个框架,可下一个句子的核心意象已经飘过来,不容他片刻迟疑——他要抓住它。于是,句子与句子你追我赶地彼此连缀,它们看起来有些言不及义,实际上却严格遵循着一种逻辑:弥漫于整个爵士时代的如极昼般的色彩,那种只知今朝有酒的凌乱的切分节奏,都在为这种逻辑背书。 他的句子总是繁复到叮当作响,却还是跟不上自己奔逸的思路,写到最后似乎总欠一点重物坠住整个框架,可下一个句子的核心意象已经飘过来,不容他片刻迟疑——他要抓住它。于是,句子与句子你追我赶地彼此连缀,它们看起来有些言不及义,实际上却严格遵循着一种逻辑:弥漫于整个爵士时代的如极昼般的色彩,那种只知今朝有酒的凌乱的切分节奏,都在为这种逻辑背书。
他,是菲茨杰拉德。
他44岁的人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好几页理不清的话题
他比很多作家都更懂得自己的商业价值,他知道自己在纽约年少成名的实质是什么——“转瞬之间,还没来得及证明我担任不了这个角色,我,这个对纽约的认知比不上任何一位上任六个月的记者,对社交界的了解比不上任何一个纽约里茨饭店大堂男侍应生的家伙,就被人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非但要担任‘时代发言人’,而且要充当那个时代的典型产品。”在广告公司讨生活的短暂经历似乎教会他自觉地在身上涂满胶水,好迎合各种霓虹色的时尚标签。但也正因为知道那些都只是标签,所以他从来没有一分钟享受到安全感。某个下午,他乘着一辆出租车从高高的大楼之间驶过,头顶上是紫红与玫瑰红混杂的天空,然后他开始嚎啕大哭,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知道以后再也不会如此快乐了。
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披露明星作家“在‘人间天堂’袭警”。《人间天堂》,正是他那部一鸣惊人的处女作。当这几个字被编进新闻段子时,他觉得它们既熟悉又陌生,就好像此刻让他回忆昨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一样。他徒劳地回忆着,但什么都想不起来。其实也无所谓,他对周遭环境的态度是“以某种于斯曼式的固执来打量这座城市”,他的行动路线是“穿过一道道奇特的门,走进一间间奇特的公寓,终于与纽约融为一体”,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们挥霍无度,但我们还保留着某种近乎戏剧性的天真,而保留天真的方式就是宁愿充当被观察者而非旁观者”。
“被观察者”如他,知道镜头无处不在,知道自己的“挥霍”也体现着职业精神。他带着他的“物质女郎”泽尔达周游世界,把在时尚杂志开专栏挣来的每一个美元都浪掷在各家酒店里,然后,半是玩味半是厌弃地,他和泽尔达一起写——写下每个酒店的独特气味和荒诞画面:
“巴黎的德蒙德饭店位于一个蓝色的幽深莫测的庭院尽头,那庭院就在我们窗外。我们犯了个错误,把女儿放在坐浴盆(即bidet,法国人发明的专用于清洗下身的盆)里洗澡,第二天,她还把杜松子酒当成柠檬水喝下去,把午餐桌搅得乱成一团。”
“紫藤蔓低垂在阿维尼翁的欧罗巴饭店的庭院里,售货车载着曙光,辘辘前行。一位身穿粗花呢的女士在光线黯淡、邋邋遢遢的酒吧里孤零零地喝着马提尼。我们在丽舍饭店与法国朋友会面,聆听傍晚时分回荡在城墙间的钟声。教皇的宫殿如同一个匪夷所思的梦,穿过金色的余晖,耸立在宽阔宁静的罗讷河上,而我们则在对岸的法国梧桐下,一丝不苟地,无所事事。”
……
以后呢?以后的故事可以用《夜色温柔》的情节去比照——发疯的妻子,枯竭的才子,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破产,也可以借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一句话(他极少写这样短的句子)来概括:“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直至辞世,他以44岁的人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好几页都理不清的话题,在“二十世纪百部英语小说”里占掉两个名额,并且在身后成为村上春树等人的终生写作标杆。我们都知道,他叫F.S.菲茨杰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