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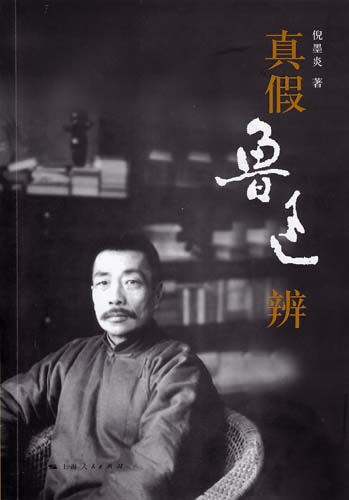 编成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编成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赞成:学术讨论应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即使有人恶意攻击,也就把其攻击公之于众,仍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力图这么做的,但不知效果如何。例如,关于“鲁茅信”,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尤其是第二篇,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完全是就事论事的。不料陈漱渝、陈福康各发表文章,远离学术讨论的原则,进行政治陷害式的攻击。这样我被迫写出第三篇文章与之辩论,因为不辩不足以明史实,不辩不足以明是非。我又写第四篇文章,完整地展示陈漱渝的一段文字,请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假霸风”的表现。后两篇文章,我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四篇文章编在一起,结构紧密,所讨论的问题步步深入,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又如,关于段祺瑞政府是否通缉鲁迅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的,是史料性的,是客观的。不料陈漱渝又撰文表示反对。我的第二篇文章仍不点名,仍摆事实、讲道理,仍是心平气和的,但全部内容乃至各小标题,都是回答陈漱渝的质疑的。我又写第三篇文章,展示一些史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假霸风”的源头及其怎样渗透到《鲁迅全集》的注释的。三篇文章编在一起,我感到很完整,论证是一步一步深入的。
为了写本书中的几篇重头文章,从2006年至目前的2009年,共花了将近四年的宝贵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中断了正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晚年周作人》的写作;还有一部字数更多的大稿,本来计划要定稿好几章的,也只好暂停。一些知情的朋友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我能编成本书,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1)我理清了那么多被搞乱了的鲁迅的生平大事;(2)我指出了“假霸风”的客观存在,它是我们鲁迅研究发展中的最大阻力。
因此,编完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花去四年宝贵的人生时间,值得!
写成本书,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的不少重头文章,是先后发表在《文汇报·学林》专页上的。主编陆灏先生三十年前刚从大学出来,任《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我们就开始交往。拙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刚出版时,他是来寒舍采访的第一位记者,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在文汇报社内好几个部都工作过,有一个时期他竟去了经济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联系,但我有什么小书出版,一定送请他指教。正因为他能在各个部门“闯荡江湖”,所以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才能胜任《学林》的主编。他很有主见,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如果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或写些套话空话,肯定遭遇退稿。他喜欢言之有理的创见,不怕冒风险。拙文《唐弢〈琐忆〉真实性质疑》,打听下来,一些专业性的刊物顾虑重重,我寄请陆灏看看,他很快就发表了。有些文章我在写之前先与他联系,他总是关照: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客观公正,不要情绪化,不要点名。像“鲁茅信”探讨的长文,像段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两篇长文,像鲁迅诗稿出版“无假不成书”的长文,像鲁迅故居的陈列应尊重历史原貌的长文,都是遵循他的关照写成,发表后反响很好。他自己也喜欢动笔,已有《东写西读》等著作出版。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编者,就是刘绪源先生。我们相识已有三十多年,而关系最密切的,也是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文艺评论,是全能作家。他所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一版、二版、三版,前些时报上有一篇长文评论,称它是当前儿童文学研究的“准经典”著作。他在周报时,有的文章有几种设想,我常常在电话中向他请教哪种写法较好。近年他任《笔会》主编,本书中有不少篇就是由他发表的。我的文字粗疏,不少编者帮我润色,而绪源兄的修改常常使我感到意外的精彩。《文汇报》还有一位编者对我很有帮助的,那就是郑逸文女士。她也很有独到的编辑思想。本书中有些文章,是发表在她主编的《文艺百家》和《书缘》上的,十分感谢她的宽容和友好。感谢《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编辑部的热情。感谢《档案春秋》接连发表我的几篇长文。《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在该刊发表后,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为《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人民政协报》等七家报刊所转载。
|